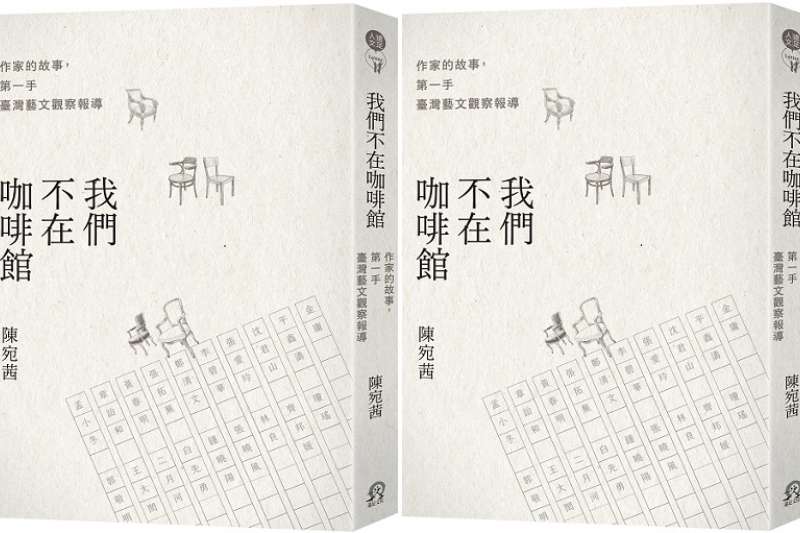一代青衣顧正秋辭世消息曝光後,電視臺跑馬燈打上「蔣經國追不到的女人」當標題。顧正秋女兒任祥告訴我,那一整天她不敢看網路、也不敢看電視,心中有所準備:對京劇藝術陌生的世代,對一代青衣的記憶只剩下了八卦。
還沒見到顧正秋前,我已先閱讀了她的三本自傳。第一部是一九六六年的《顧正秋舞台回憶》,第二部是一九九九年的《休戀逝水》;以及二○○五年的《奇緣此生顧正秋》。這三本自傳都沒提到蔣經國。
一九四九年,顧正秋帶著顧劇團來臺,進駐大稻埕的永樂戲院。她原本只想演出三個月,卻遇上兩岸決裂,臺灣從此成為第二個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連演五年、上百齣京劇戲碼,用戲曲的離合悲歡撫慰遊子的鄉愁。
蔣經國和財政部長任顯群都是座上客。傳言兩人競爭顧正秋,任顯群最終贏得美人心。顧正秋和任顯群婚後保持低調,某天相偕參加師妹張正芬婚禮,遭報紙頭版曝光。沒多久任顯群便以匪諜的名義遭捕下獄,江湖盛傳這是情敵的報復。
傳言傳了半世紀,當事人沒一個吭過聲,任憑外界捕風捉影。顧正秋出第一本傳記還在戒嚴時代,沉默是明哲保身。出第二本傳記小蔣總統已辭世,記者問為什麼不寫,她說「因為人(蔣方良)還在」。但第三本自傳面世已是蔣方良身後,她依然沉默。
隔了那麼遙遠的時代,我卻還能聽到陳年舊事掉下來的碎屑。數年前我採訪明星咖啡館老闆簡錦錐,他給我看一張蔣經國和蔣方良在「明星」合照的照片,照片中蔣經國把手放在蔣方良肩上。簡錦錐說,那時蔣經國追顧正秋的八卦傳得沸沸揚揚,蔣經國拿這張照片跟他開玩笑,說照片中的自己「看起來像是要把蔣方良掐死」。
任顯群出獄後,和顧正秋攜手到金山農場開墾。顧正秋封嗓引退,除了寥寥可數的幾次義演,不再登上舞台。退隱那年她廿五歲,正是角兒顏值和演技並盛的黃金歲月,如此決絕令人不解。研究戲曲的學者王安祈告訴我,在那樣的年代,她知道要繼續經營劇團,難了。
任祥童年在荒涼的金山農場度過。她告訴我,母親在家中放了一箱戲服藏住過往的流金歲月,每回曬「壓箱寶」,一件件頭飾、霞帔在荒野中晃盪,光彩奪目。任祥看得目眩神迷,中國文化之美在她心中留下燦爛的光影。她長大後出了一套四冊的《傳家》,把母親傳給女兒的中華文化之美與智慧寫得淋漓盡致。
顧正秋的「顧腔」千迴百轉,動亂的時代特別能勾起遊子的柔腸百轉。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少年從軍時在南京聽過她的「蘇三起解」,說那句拐了三個小彎的「蘇~三」,放在他心中就是一輩子。我問王安祈聽過顧正秋唱戲嗎?她說,生平就只聽過一次,是顧正秋為了國家戲劇院開幕重披戲衫的經典演出,「能聽到顧腔,那需要福分啊。」
期待那樣的福分,我來到了陽明山上任祥的家。那一天,大陸國家京劇院剛跟顧正秋簽約,要將顧正秋自傳《休戀逝水》搬上京劇舞台。女兒任祥為母親辦了一場「票房」,邀京劇迷到家中票戲。我盤算著,除了一聽顧正秋「人間難得幾回聞」的顧腔,還可以問問她,華人世界都想知道的歷史之謎。
(相關報導:
季季專文:顧正秋的骨氣
|
更多文章
)
在任祥的客廳裡,我第一次正式採訪顧正秋。過去在文獻資料上看顧正秋,總覺得她的眼神在昏黃褪色的紙張上燦爛流轉,彷彿有故事要說。見到本人,青衣變成老旦,眼神依然流轉,裡頭藏了人生的千迴百轉。
提起人生將從台下搬到台上,顧正秋表示,她的傳記都講真話,「不加鹽不加醋」,她對改編的要求也是「真」。這一生學了上百齣戲,顧正秋認為京劇的精華是「忠孝節義、教化人性」,自己的人生觀與道德觀、價值觀,都是從舞台上學來。
來臺前,顧正秋在上海看麒麟童演「明末遺恨」,其中一段她記憶猶新。崇禎帝去找臣子,發現國將敗亡,朝中卻仍絃歌不輟,「這不是就是當時中國的寫照?」她說,京劇濃縮了中國人政治和人生的智慧哲理。
顧正秋曾拜京劇大師梅蘭芳為師,向程硯秋、張君秋等名角學戲,「他們不只是我學戲的老師,更是我人生的導師。」她感嘆現代許多學生學戲不再「拜師」,只從錄影帶學身段唱腔,忽略「學戲也是學人生」。
顧正秋說戲就像說人生,我聽得入了迷,忘了問問題。當我準備開口時,她似乎察覺我的意圖,微笑說:「戲要開鑼了,快去聽戲吧。」
我想著,下一次,下一次一定要開口問她這個問題。然而半年後顧正秋離世,我永遠失去了發問的機會。
任顯群。蔣經國。蔣方良。顧正秋。在這齣橫跨政壇與藝壇、融合政治和愛情的大戲中,顧正秋是四位主角中最後下台的。對於這件歷史公案,她說了算,擁有至高無上的發言權,沒有人可以反駁她。但她選擇了沉默,對於這件改變了她一生的事,她一生無言。
我看過太多人用自傳找公道,用文字進行最後的復仇。有人說顧正秋隱忍,有人說她寬大、有人說她委曲求全。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智慧,從戲曲中學來的智慧,中國幾千年的智慧。
如果顧正秋寫了蔣經國,那她的自傳從此成為八卦的文本,讀者讀的永遠是那一段,她將被貼上撕不下的標籤「蔣經國追不到的女人」。逝水不再澄澈,而是黃沙滾滾。
她沒寫,前塵舊恨在她來說就只是過場,曾經翻雲覆雨的弄潮兒連配角都不是。在她自己的舞台上,顧正秋就是顧正秋,永遠的一代青衣,不是誰的誰。
拍板響起、京胡幽幽流洩樂音。那一夜,任祥的客廳變成永樂戲院,票友輪番上台唱戲。當年的座上客郝柏村從權傾一時的行政院長退下,八十歲後開嗓學唱京劇,他一亮嗓唱起諸葛亮的「空城計」,彷彿引動滔滔的歷史浪潮在我們面前滾動。顧正秋在台下微笑聆聽,眼神幽幽流轉;一整晚,她都沒上台。
從台上到台下,此時的顧正秋,心中必然感慨人生如戲。
我悵然若失,沒機會聽到人間絕響顧腔。王安祈告訴我,頂尖角兒不輕易露嗓,只會把最完美的表演展現給戲迷。任祥也說,從小就知道媽媽愛聽戲、看戲,卻極少在她面前唱上一段。
戲台上的角兒,往往最重視初登場的「亮相」,追求一亮相便豔驚全場。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也是永樂戲院裡的「顧粉」,曾告訴任祥,顧正秋唱戲,最美之處不在「亮相」,而是「下台的身影」。她每次下台,蓮步輕移、衣履不搖,優雅而從容迅速,不留戀也不遲疑,是完美的典範。
任祥這樣形容母親的「顧式謝幕」:「每一場成功演出,觀眾的情緒總是異常的讚嘆,踴躍的鼓掌請她出來謝幕,而她總是緩緩的往舞台中間一站,謙虛地向台口中間一鞠躬,左邊一鞠躬,右邊一鞠躬,表達了她對觀眾的感謝後,即迅速的離開舞台,她似乎從不留戀觀眾給予的熱情讚美。對她而言,表演工作者展現完美的演出是應該的。」
上台靠天分,下台靠智慧。優雅而從容,不留戀也不遲疑。顧正秋這樣的謝幕,在這個時代也是絕響了吧。
(相關報導:
季季專文:顧正秋的骨氣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