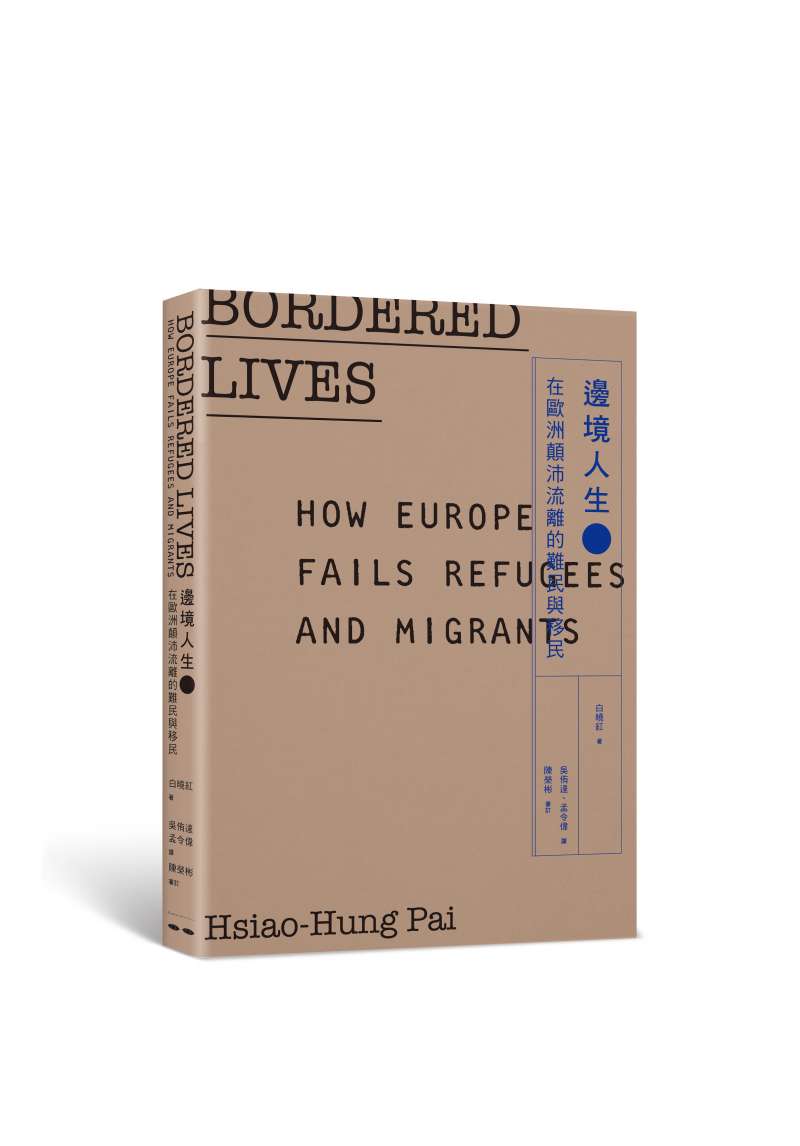之前我在街上遇到的孟加拉少年札希德告訴我,他在離開利比亞前曾與人蛇集團打過交道。「那些跟利比亞當地的企業與工廠老闆合作的孟加拉人口販子招募我們入夥工作,然後欺騙我們。我們在利比亞的工廠裡成了奴工。當時我們對自己的工作與這個國家一無所知。」
那時,這三位青少年被送進陶瓷工廠工作,領不到半毛錢。阿西夫問了關於薪水的問題,反而遭到監禁。他不斷被毆打、折磨, 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會被關多久。說著說著,阿西夫舉起手臂,展示毆打留下的傷痕。那黝黑的瘀血迄今仍未消去。他們異口同聲說, 利比亞的生活跟地獄並無二致。
札希德說:「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時期,沒什麼比這更慘了。」回憶這段痛苦的過程,他看來很驚恐,甚至開始喘不過氣。這段記憶帶來的恐懼,排山倒海而至。「去利比亞是我們犯下最大的錯誤。」
一個月後,阿西夫終於跟他的獄友成功逃離利比亞監獄。後來他加入了從工廠逃離的札希德還有賽伊德。他們輕易找到了當地的人口走私販子。由於所有利比亞走私者都知道自己能剝削這些亟欲逃離利比亞的青少年,且這裡絕大部分的工廠工人都是孟加拉人, 因此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孟加拉裔少年。三人向家人求援,每人付走私者一千歐元(約新臺幣三萬六千元)讓蛇頭用船隻販運他們去歐洲,同行的還有來自摩洛哥及其他非洲國家的人。
當時的利比亞處於無秩序狀態, 是迫使成千上萬人逃往義大利的主因之一。這種混亂狀態背後的形成脈絡,顯然要追溯到二〇一一年。當年,在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下,利比亞人開始走上街頭力籲改革。獨裁者格達費(Muammar Qadafi)隨即鎮壓人民的反動。北約組織為首的西方陣營對利比亞實施武器禁運,轟炸格達費的軍事據點。因政權轉換而進行的軍事介入最終導致格達費倒臺與死亡,也間接促成過渡政府成立。至此,利比亞陷入無止盡的內戰, 各方軍閥為控制權而爭鬥,秩序崩壞。情況在近年變本加厲,深陷其中的移民別無選擇,只能逃離此地。

札希德回憶當時情況:「那艘船限重三十人,船上卻有六十五人。引擎在中途就壞了⋯⋯我們得用手划船,所幸最後獲救,才被送到蘭佩杜沙的營區。」他講到這裡就停下了,但我很確定他的經歷比實際說出口的還多。到了本章稍後,我們將看到他透露出更多關於渡海的細節。
抵達蘭佩杜沙前一週,三人的指紋就已遭採樣。不幸的是,他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出發。他們前方是充滿不確定的未來。
抵達營區後,他們對裡頭的惡劣環境感到震驚。一個房間居然必須容納多達二十五人,每人分到的不過是「睡眠空間」。房間裡共有三層床鋪,札希德跟阿西夫分到最下層,基本上就是水泥地板。地上連塊床墊都沒有,也沒有被子。
一天雖有三餐,但分量完全不夠。不只分量不足,食物的品質也教人難以下嚥。問題不是他們得花時間適應義大利菜,而是營區根本沒有好好處理食物。食物不是腐壞就是沒煮熟。
難道這就是營區要移民習慣的人事物?這幾位男孩常如此自問:「這是我們應得的嗎?」 (相關報導: 在「外人」的位置理解他們:《憤怒的白人》選摘(4) | 更多文章 )
除惡劣的環境外,營區還有一些在移民眼中根本不合理也不公平的規則。札希德告訴我:「營區禁止我們從前門進出,我們沒有外出的自由。所以如果我們想透透氣,只能從營區後的籬笆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