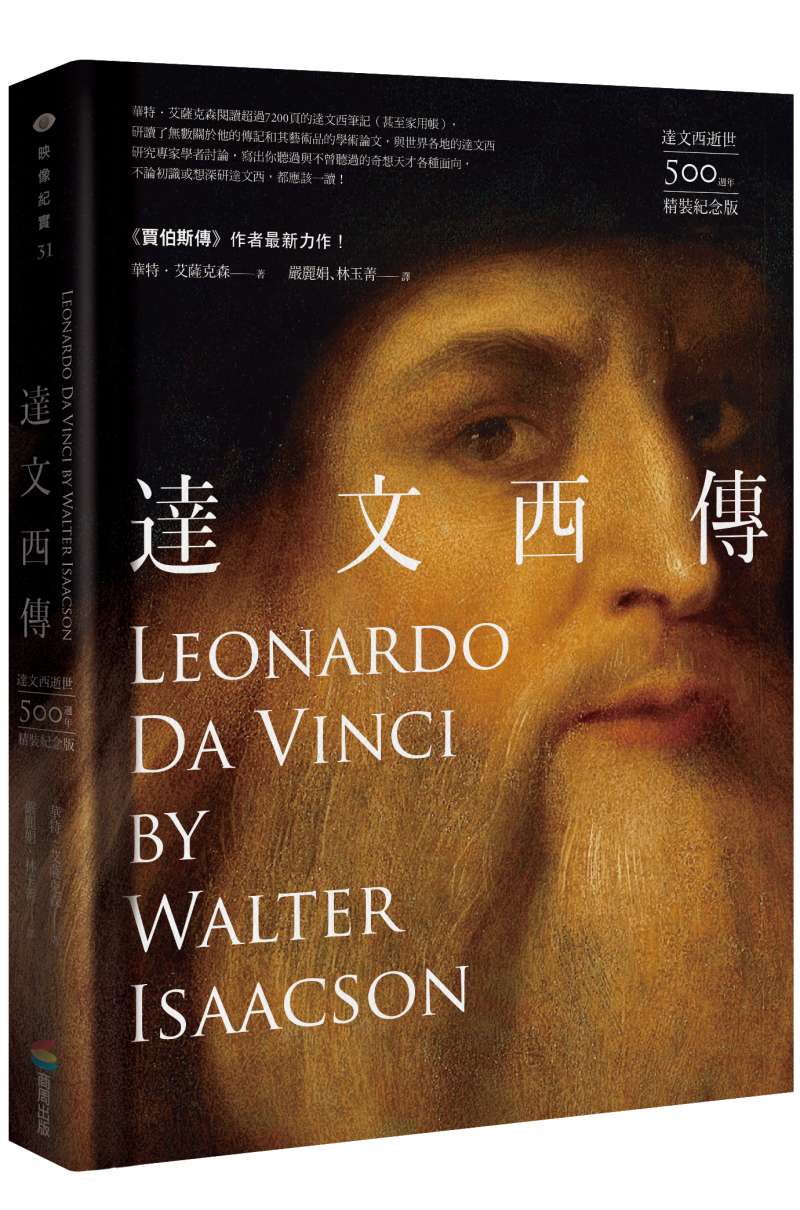達文西發覺,繪畫的藝術和光學的科學脫離不了透視法的研究。除了適當配置陰影的能力,精熟各種透視法後,畫家就能在平面上傳達出立體的美。要真正了解透視法,不光只會按著公式正確畫出物體的大小,也需要研究光學。「繪畫的基礎是透視法,」他寫道,「透視法就是對眼睛機能的完整理解。」因此,在撰寫計畫中的繪畫和光學論著時,他也收集想法,準備寫透視法的論文。
在佛羅倫斯的少年時期,達文西在《三王朝拜》的稿本裡費盡心思處理透視法的數學。他畫出的格子就是嚴密套用阿伯提的概念,看起來非常不自然,跟馬兒和駱駝討喜的想像動作一比,更有這種感覺。可想而知,他開始畫最終版本時,調整了比例來展現出更像想像的畫作,其中的線性透視法無法束縛動感和幻想。
跟其他很多主題一樣,在1490年代早期正式加入米蘭公爵宮廷的智力溫床後,也刺激達文西認真研究透視法。1490年到附近的帕維亞大學參觀時(也在那次旅途後畫出《維特魯威人》),他跟法齊奧.卡爾達諾(Fazio Cardano)討論了光學和透視法,這位教授為約翰.派開姆在13世紀寫的透視法研究編輯出第一本印刷版。
達文西的透視法筆記混在光學和繪畫的筆記裡,但他似乎想為這個主題獨立寫一本論著。16 世紀的藝術家本威奴托.切利尼說他有一本達文西的透視法手稿,他說這是「人類創造出最美的書籍,顯示物體不只按透視法縮短深度,也會縮短寬度和高度。」洛馬奏則說這本書「寫得很晦澀」。他對透視法的訓誡有不少流傳下來,可惜這本手稿已經佚失了。
達文西擴展了透視法的概念,不光納入線性透視法,用幾何學來找出繪畫中前景和背景中物體的相對大小,也透過顏色和清晰度的變化來傳達深度,這是他對透視法研究最重要的貢獻。「透視法有三個分支,」他寫道,「第一個處理物體從眼前往後退時的明顯縮小。第二個講到後退時的顏色變化。第三個則涉及圖畫中的物體變得更遠的時候會怎麼流失細節。」

至於線性透視法,他接受比例的標準規則:比另一個物體離眼睛兩倍遠的物體「看起來只有第一個一般大,但真實的尺寸可能一樣,在空間加倍時,縮小度也加倍。」他發現這個規則可以用來畫正常的大小,這時候邊緣跟觀畫者的距離並不會超過中心和觀畫者的距離太多。但如果是大型壁畫或壁飾呢?邊緣跟觀畫者的距離可能是圖畫中心和觀畫者距離的兩倍。「複雜的透視法,」這是他的說法,此時「表面看起來絕對不會跟平面本身一樣,因為看到表面的眼睛跟四邊有不一樣的距離。」他馬上會讓我們看到,牆壁大小的畫作需混合自然的透視法和「人工的透視法」。他畫圖解釋說,「非人工的透視法,指不一樣大小的物體放在不同的距離時,最小的比最大的更靠近眼睛。」 (相關報導: 藝術家到底需要什麼特質?會畫畫就可以了嗎?聞名世界的畫家孟克給的三大建議 | 更多文章 )
他並不是研究線性透視法的先驅。阿伯提已經解釋得差不多了。但達文西更為創新,把重點放在敏度透視法上,描述遠處的物體怎麼變得更模糊。「物體離觀眾的眼睛愈來愈遠,你必須按著距離增加的比例降低這些物體輪廓的鮮明度,」他這麼指示其他畫家,「在前景比較近的部分,要用大膽、有決心的方法畫完;但在遠處的必須有未完成的感覺,輪廓模模糊糊。」他解釋,因為遠處的東西看起來會比較小,物體上的微小細節消失了,然後連比較顯眼的細節也開始消失。在很遠的地方,連形體的輪廓也難以分辨。他用城牆外的城市和塔樓當成例子,觀畫者看不到底部,可能也不知道大小。把它們的輪廓變模糊,敏度透視法就能指出這些結構在很遠的地方。「很多人在呈現離眼睛很遠的小鎮和其他物體時,把建築物的每個地方都畫得跟很近的事物一樣,」他寫道,「這不是大自然中的景況,因為我們無法察覺遠處物體的確切形體。畫家要是像某幾個那樣,凸顯出這些輪廓,以及各部位的微小區別,就呈現不出物體很遙遠的感覺,犯了這樣的錯誤,會讓它們看起來非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