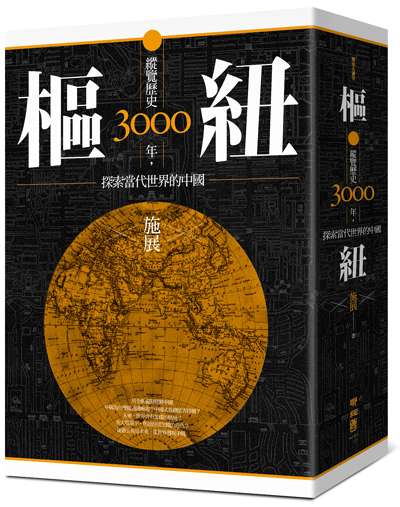中國的經濟持續不斷地深度融入全世界,由於中國的超大規模體量,我們純粹內政的行為,也會產生巨大的外部性效應。這些都使得我們過去對於世界的認知模式遭遇嚴重挑戰,無法真正意義上地理解自身與世界。倘若始終無法獲得「林肯論辯」式的認知與理解方式,中國將無法理解外部世界的正常訴求,即便是外部世界發起談判的請求,也可能會被中國視為圍堵而遭拒斥。
可以說,此時的中國需要的是一場「精神解放」運動,而不僅僅是一場啟蒙。這裡的所謂啟蒙,是指在蒙昧的狀態下開眼看世界;所謂精神解放,是指在根本上改變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啟蒙可能帶來大量的資訊,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幫助我們去理解這些資訊的意義為何。因為,任何資訊,都只有在特定的認知框架下才會呈現出其意義,沒有脫離開認知框架存在的赤裸資訊;同樣的資訊,在不同的認知框架下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而所謂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構我們的認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無法簡單地通過另一次啟蒙來完成的,因為這很難突破觀念論的結構,只不過會讓我們落入新一階的將民族理解為緻密體的誤區。「林肯論辯」的意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浮現出來,它有兩重意涵:第一,我們需要有歷史政治觀上的轉變,對世界秩序進行全新的理解與實踐;第二,中國需要在精神層面上進入不斷自我解放的過程,它可以通過林肯論辯的方式進行。新的歷史政治觀在此論辯中浮現出來。
林肯的《蓋茲堡演說》不到300字卻名留青史。(圖/Jeff_Kubina@維基百科CC BY-SA 2.0)
視野進一步打開的話,可以說,在世界層面上也需要開展國際交涉的「林肯論辯」。歐洲歷史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啟示。二戰前歐陸的民族主義都是觀念論的歷史政治觀,它們都指向特殊主義的、割裂普遍空間的世界秩序想像,這些緻密體之間的理念關係是「命運對決」,無法進入「林肯論辯」。二戰後的歐洲統一進程,終於超越了那種特殊主義的秩序觀,歐洲內部的安全問題不再成其為問題,於是一種「林肯論辯」的過程在歐洲框架下展開了——從早期舒曼、莫內關於歐共體的聲辯,科爾關於德國統一的應急設計,到德斯坦領導的歐洲憲法討論,再到近年哈貝馬斯對歐盟的警示演說,林林總總。經貿過程走上了與政治過程合一的進程。這段歷史可能是未來世界歷史發展的某種小規模預演。
就世界秩序而言,還有著超越於歐洲乃至西方之上的更深一層的普遍性,這就需要「林肯論辯」在幾個世界歷史民族之間繼續展開。它將重構這些世界歷史主體的自我意識,世界秩序最終進入一種去主體的主體間性的進程之中。這樣一種論辯,將是對中國的全球歷史意識的發現過程,會促成中國的精神解放。它既要在中國內部來展開,也要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尤其是中美之間來展開,這裡涉及的不僅是中國發現自己的全球歷史意識的問題,也涉及美國的全球歷史意識的重構問題。
對美國來講,它面對著怎麼消化中國乃至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的問題。消化的第一步當然是理解對方,而這種理解不可能純粹觀念運動式地完成,它一定要進入一種「林肯論辯」的過程才可能展開。在這個理解、消化的過程中,美國將改變自己,改變自己的文明樣式,改革自己的政治存在方式。中國也一樣,在與美國相處的過程中,改變自己,達到那樣一種變化。這是一個真正宏闊的世界歷史過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意識如何從彼此茫然無知,到彼此深存誤解,最後彼此實現和解,達致一種普遍秩序。
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中國被還原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環節,美國也被還原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環節。這個世界歷史過程的完成,表現為世界秩序的普遍司法化。現代政治的意識形態所構造出來的政治空間,在「林肯論辯」的時間維度之展開中,形成一種真正的普遍秩序。在此普遍秩序中,國家變成財政單位,變成社會福利組織單位,民族成為多樣化的文化形態,變成日常生活方式。
這是對同時包含著時間與空間之雙重維度的古典帝國的某種回歸。作為空間存在的國家,在「林肯論辯」的時間維度中與世界不斷互動,與世界秩序共同演化;「憲法典」敘事中對時間維度的屏蔽,共產主義敘事中對空間維度的屏蔽,因此而全部獲得突破。古典帝國「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這回還可以加上「文化的歸文化」。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基本的政治單位,其政治性消散於普遍秩序之中,民族國家時期構建起來的列強體制,也就漸漸退縮在諸歷史主體的普遍聯繫之中而被徹底克服;對歷史的敘述,終能祛除政治的遮蔽,作為歷史而回歸。
這樣一個過程,就是人類普遍憲制展開的過程。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秩序的衝擊以及對中國自身的改造,帶來普遍憲制展開的可能性。其過程不會一馬平川,必定多有反覆,這也是「林肯論辯」的常態,但從長線來說,其方向不會有變。這在更深的意義上籲求著中國精神格局的轉型,以便從自覺意識上讓中國與整個世界歷史進程逐漸融合在一起。當我們達到這個轉變的時候,就消除了民族精神分裂和精神內戰的可能性,從而成為一個精神飽滿的民族,一個自我實現了的民族。
基於對這樣一種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中國必將自己的現代轉型最終落實為憲制,在制度層面上將自己的內政秩序與國際秩序聯立起來,從而在實力、理想、制度三個層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義轉型。這個過程會進一步推動人類普遍憲制的展開過程。中國的憲制不可能通過一次簡單的立憲活動而實現,因為其內涵遠超一部簡單的憲法典。它必須能夠結構性地反映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反映中國作為世界之全息縮影的現實;將中國複雜多樣的現實統合在統一的法權秩序當中,既承認超大規模國家內部地方主義的正當性,又不導向國家的分裂;在技術上使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日常政治既能有效運作,又不至於喪失對人民的代表性;對於中國的悠久歷史、澎湃的革命史以及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都能吸收並表達在憲制的理想當中。
2018年3月11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包括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在內的修憲案(AP)
對這個憲制不能做法典化的理解,而需要做歷史性的理解,但它又必須呈現為法典化的形式。
這樣才有可能讓前述所有這些彼此之間經常有著巨大張力的要素,都在這個自由憲制中獲得其表達;才能將前文反覆討論的世界政治與國家政治當中的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之間的張力給出恰當的安頓,讓中國與世界的共同演化過程,通過該憲制作為制度性介面,而獲得恰當的表達。
一旦獲得對這些意義的理解,中國的視界中將會展開一片前所未有的時空天地。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不斷努力克服自己的內在失衡的歷史。這種失衡在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都深刻地存在著;到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內在失衡以及世界的失衡,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中國內部的困境,必須在全球秩序重構的框架下,通過中國的世界主義化才能夠化解;中國的外部困境,也必須通過中國對自我意識的重新表達來獲得突破。中國的失衡需要通過一個憲制過程來馴化,世界的失衡同樣需要在一個普遍憲制過程中被馴化。
現代政治在其初起之際是以意識形態為其正當性基石的。意識形態直接塑造著人們對於世界的想像,一種觀念的而非實踐的政治理念便被建立了起來。它的極端表現,是用「觀念」取代過去的「宗教」,將政治再綁架進入一種「倫理—官僚世界」,形成一種對於民族的緻密體認識,這在現代呈現為韋伯所痛恨的「理性的鐵籠」。兩次世界大戰的源起,與這種觀念對政治的綁架有著深刻關聯。今天,在去政治化的世界,將再一次面臨被觀念所綁架的危險。在一個因為各種世界層面的失衡與挑戰而被打開的「林肯論辯」的過程中,異化了的「倫理—官僚世界」將再次獲得機會形成自我突破,真正進入到「政治世界」;而中國本身也將在這個過程中突破自己的歷史,進入到「政治世界」。
咨諸中國的歷史,我們發現其在若干輪的大循環中,內在地包含著一個自由的展開過程。中國的古代歷史便是這種自由的現實展開過程,但它到古代後期卻走向了自己的悖反,以至於無法兌現自己的軸心文明對於人性與尊嚴的承諾,從而內在地籲求著外部力量的到來。到了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通過各種形式的互動乃至互構,而朝向自由法權,經歷了艱難的轉型歷程。今天,實現了經濟崛起的中國,已經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響著世界法權。雖然從長線看,「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從中短線看,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將在深刻的意義上,決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
《樞紐:縱覽歷史3000年,探索當代世界的中國》立體書封。(聯經出版提供)
*作者施展為中國大陸知名青年歷史學者,曾發表專著《邁斯特政治哲學研究》,另有學術論文數十篇,時評文章數十篇散見於諸多刊物、媒體。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樞紐:縱覽歷史3000年,探索當代世界的中國》(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