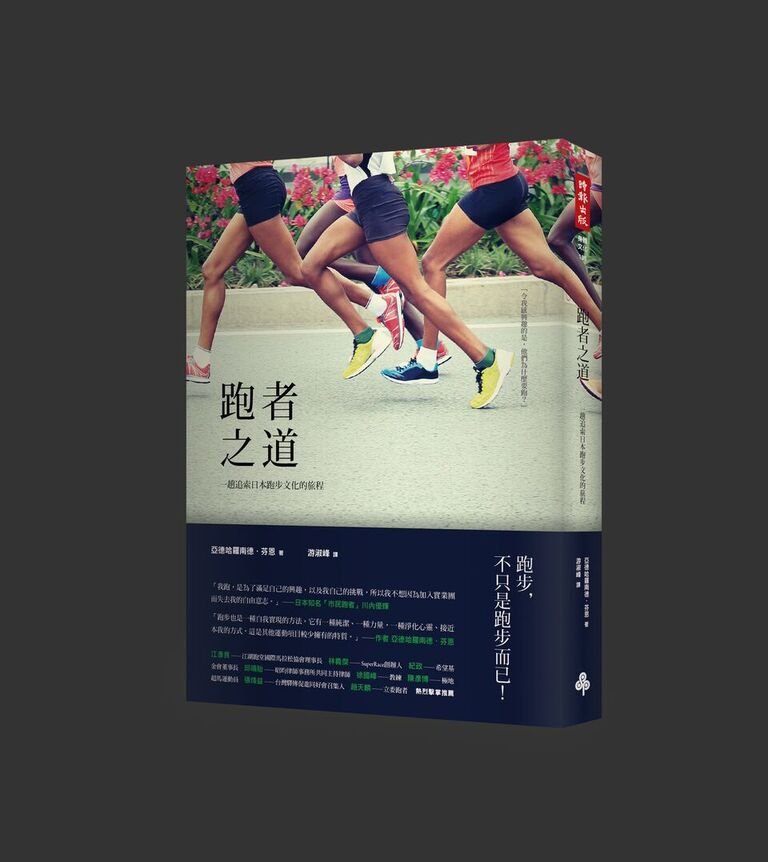「驛傳」二字,日文為「駅伝」,其起源是中國唐朝,各地為了將訊息信件以最短的速度讓皇帝得知,因此就在各地設置許多驛站,備有快馬來交替傳送信件,一站一站傳接下去到京城,這制度在唐代傳到了日本。日語與台語都遵循古義用「走」來代表跑步。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當中說:「走,趨也。」清朝的段玉裁引《釋名》說:「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
由上面解說,來看「東京箱根間往復大学駅伝競走」這段漢字,雖然是日文,但是卻能完全從字面上理解,這是一場從東京到箱根之間來回,以一站一站接力的方式,所進行的路跑賽。而「東京箱根間往復大学駅伝競走」,就是從1920年就開始,每年舉辦的「箱根駅伝」的全名,而這也是吸引本書作者亞德哈羅南德•芬恩(Adharanand Finn)在完成《我在肯亞跑步的日子:揭開地球上最善跑民族的奧祕》,揭密肯亞跑者為何能在近年來稱霸跑壇之後,再度遠從英國千里之外,探究日本跑步文化最核心的根源-驛傳精神。
日本的驚人長跑實力,讓作者芬恩大感吃驚。這也難怪,因為除了東非的肯亞、伊索匹亞之外,對他而言,日本是另一個謎樣的國家。因此,作者芬恩為了體驗驛傳精神,以第一人稱的日記式寫法,記錄了他為了親身體驗與見證的日本「驛傳競走」,想儘辦法要加入日本的實業團或大學的驛傳隊,參與訓練,以取得第一手資料,在不得其門而入之下。作者先斬後奏,趕在日本一系列的驛傳競賽舉行前夕,七月間,向公司請長假,房子也出租出去了,全家四口很驚奇的走陸路,先搭長途火車從英國到俄羅斯,再從海蔘威搭船到日本後,移居京都,進行為期六個月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
近年來跑步風潮盛行,許多人紛紛投入馬拉松或路跑活動,日本的驚人長跑實力,讓本書作者芬恩大感吃驚。。
對作者芬恩而言,「箱根驛傳」就像一個黑洞,吸噬榨乾了日本中長距離青年學生選手的所有能量。從高校時期,就被過度期待,連體格與天份明明適合跑一千五公尺中距離的選手,也被整個社會氛圍與期待,被引導甚至是強迫成為長跑選手。因此,日本學生的長跑實力,被高度期待能夠在進大學後,立即就在「箱根驛傳」舞台上,大放光芒,因此高校生被施以嚴格近乎體罰式的嚴格管教與訓練。作者不時在書中,將日本與英國甚至東非對比,他認為在日本不光是高中生,連大學生的訓練都是揠苗助長。
這也難怪,因為日本高一學生的五千公尺記錄,在2014年,首度由遠藤日向跑進13分台(13:58),日本高校生記錄則是佐藤秀和13:39,反觀,我國全國紀錄則是吳文騫的13:54,而台灣歷史上也僅有吳文騫一人跑進13分台。也就是說,當前日本頂尖高中一年級學生的長跑實力,已經可以稱霸台灣,更遑論大學生。
當然,透過一個英國人的眼光,進入異文化的日本,其文化震撼後所觸覺到的細微差異,可能是我們所忽略的。例如:作者認為,日本人在家居生活上,少坐椅子,大都跪坐在榻榻米上、還有西方人難以挑戰的蹲式馬桶蹲法,作者都嚴格地加以分析,認為可能有運動生理學上的影響,提升了日本人的天生長跑能力。
(相關報導:
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和真相: 《中國幻象》選摘 (1)
|
更多文章
)
不過,日本人的驚人長跑實力,絕非體格上的生物性特異功能,毋寧說是社會性的集體產物,其結晶就是「驛傳」。而為了一窺驛傳精神,作者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近乎耍賴的手段,試圖打入日本高度嚴密封閉的集體組織,卻也誤打誤撞同時觀察到了日本的驛傳競走,是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再到實業團與社區,鑲嵌在整個社會組織當中的龐大體系。
日本的大型馬拉松,猶如海明威筆下的二十世紀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取自大阪馬拉松粉絲專頁)
首先他參加所居住社區居民所組成的驛傳隊,並參加社區比賽,進而結識京都立命館大學男子陸上部監督,並見證了該校在全日本大學驛傳的分區預賽慘遭淘汰,這些年輕的大學生與監督,如何面對來自校友、家長、同校同學與校方等人的強大同儕團體壓力。
後來作者又成功混進,前來日本參加「出雲驛傳」的美國長春藤聯盟大學代表隊,反正日本人也分不清英國人與美國人,讓主辦單位以為他是隊員之一,得以第一手記錄這些首度踏上日本土地的美國選手,對日本社會,竟然對長跑選手竟然如此熱情與狂熱,感到不可思議與無法理解。
更幸運的是,作者竟然與日清食品實業團陸上部搭上了線,並與陣中的超級巨星佐藤優基、村澤明伸與眾肯亞好手共同訓練,當然他只跟的上前五公里,不過因此訓練機會,作者與曾到美國受訓通曉英語的村澤明伸成為好友,探究到日本頂尖職業選手的內心世界。
本書最後的高潮,當然就是作者以新聞記者身分,到東京實際觀察了從1920年就開始,目前每年固定在一月二日、三日舉行的「箱根驛傳」:從東京到箱根之間,來回約217公里,共十區間的比賽。這是一場電視直播收視率達30%,沿途現場加油民眾超過百萬的嘉年華會般的賽事,但毋寧說這根本是一場集體狂歡的祭典。而能夠站上箱根賽道的兩百名各關東地區的大學選手,幾乎是日本青年長跑選手菁英中的菁英,但也是這些大學選手承受巨大社會集體壓力的精神考驗。
日本的驛傳精神所蘊含的團隊榮譽至上集體主義,作者芬恩認為其把年青選手心中的可能的小宇宙給壓的透不過氣進而摧毀,特別是監督的權威與軍隊式管教方式,導致日本近年來在奧運馬拉松成績低落。他以他親身觀察的2014年90回箱根驛傳,由以作風開明著稱的年青監督酒井俊幸,所領軍的東洋大學,擊敗以傳統家父長嚴厲訓練著稱的監督大八木弘明所領軍的駒澤大學,作者芬恩以此驗證他的想法。不過他可能沒想到在之後兩年的箱根驛傳,會由作風更開明自由,業務員出身的原晉監督,締造青山學院大學二連冠的霸業。
在大阪,馬拉松比賽儼然成為行銷這座城市的歡樂嘉年華,市政府將當地最有特色的街道和景觀留給跑者,市民也全情投入,甚至為此引以為傲。(取自大阪馬拉松粉絲專頁)
當然,順著這個脈絡,作者芬恩自然是絕對不會放過特立獨行於驛傳體系之外,目前任職於高中母校夜間部公務員的「市民跑者」川內優輝(全馬2:08:14,日本歷代第19位)。芬恩又混進了一場賽後記者會,當面問了川內幾個問題,之後川內又以電子郵件回復了作者的詢問,更深入探討了日本驛傳體系的得失,川內並表達「我想要展現給前途看好的年青跑者看,不需要教練,自由自在地跑是多麼有趣的事。」
以西方個人主義盛行,強調個人競爭的英雄主義社會環境,自然很難想像,日本這種強調為團體榮譽犧牲個人的武士道社會傳統文化,更很難想像,連跑步如此個人化的運動,在日本的驛傳體系之下,能夠演變成如此集體化。
本書讓很多西方人,其實也包括大部分的台灣人,揭密了日本的強調團隊榮譽的驛傳精神,在過去對於培養長跑選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凡事都有一體兩面,過猶不及,也造成限制與危害。
以台灣與日本驛傳體系關係最密切的許績勝教練而言,他在名古屋商科大學參加全日本大學驛傳奪得一區的區間賞,後來又進入佐川急便參加實業團驛傳的豐富經歷,使得我國馬拉松與一萬公尺全國紀錄,都是在他在日本期間締造的,就可知道日本驛傳體系之下,會激勵出多大的潛能。
雖然整本書的內容,作者芬恩在日本挖掘一輪這獨特專屬於日本特有的「跑步之道」,並描述日本的青年好手在驛傳體系之下如何被摧殘。不過當他回到英國後,參加了一場四人接力的的馬拉松賽,在驛傳精神的激勵/壓迫下,他跑出了PB並奪得團體冠軍,而他把隊名取作「Ekiden Man」(驛傳人),一個他引以為傲的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