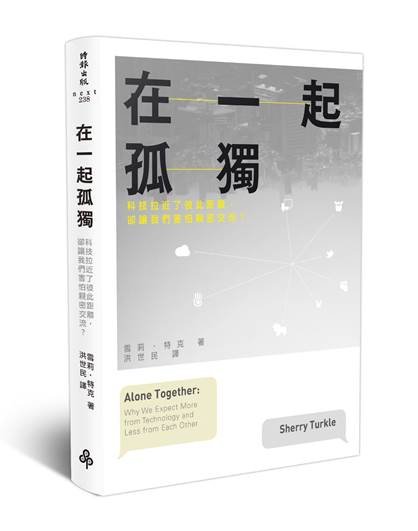那一年,《虛擬化身》(Life on the Screen)中譯本出版時,我們透過撥接連上台大椰林、批踢踢、不良牛、小魚的紫色花園。現在,我正寫著《在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的導讀。批踢踢還在,但其他BBS站台與撥接上網已成了歷史傳說。在各種行動裝置的推波助瀾下,如今以社群媒體為核心的「螢幕生活」不再只是另一個生活,它就是我們的生活。
在2000年初透過《虛擬化身》與雪莉.特克相遇,並開啟了我的資訊社會研究之旅。不過特克關於資訊社會、人與科技物關係的探問開始得更早。從1984年的《電腦革命》(The Second Self)到2011年的《在一起孤獨》,這是一場橫跨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研究。特克跟隨著當代數位科技發展的腳步,從個人電腦、網際網路到今天行動裝置與社群媒體普及、人工智慧登場,她為數位時代每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剖析了我們自身、我們的群我關係的相應轉變。
因此,《在一起孤獨》這本書的重要性就在於,這是一本由二、三十年來長期關注資訊社會、人與科技問題的重要學者,在這個社群媒體幾乎等同於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就將取代人類的時代,再一次地提出了關於我們自身處境轉變的精闢觀察與分析。在我寫下這篇導讀時,川普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有人怪罪臉書放任假新聞的傳散,並再次撻伐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同時,Google的人工智慧AlphaGo不久前擊敗了韓國棋王後,聽說又要跟著挑戰中國棋王。更不用說,關於人工智慧將使人失業的新聞早已甚囂塵上。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處境。相較於《虛擬化身》的1990年代,今天我們面對的不單純是網際網路帶來的虛擬與真實界線問題。在《在一起孤獨》一書中,特克進一步帶我們看到可以隨身攜帶的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如何使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更複雜,也帶我們看到人工智慧機器人將如何進入我們的生活。乍看之下讀者也許會覺得,人際關係的連結與人工智慧的發展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特克卻很巧妙地透過其英文書名的副標說明了兩者的共通點:「為何我們對科技的期望日漸增高,卻對彼此的期待日漸降低?」換言之,不管是我們越來越喜歡透過社群媒體互動,還是殷切盼望著人工智慧機器人的到來,背後反應的其實都是我們對彼此之間日益明顯的那份矛盾情感:我想要與你/妳在一起,卻也不想與你/妳在一起。
《在一起孤獨》這本書的意義可以放在兩個脈絡裡加以理解。一方面,在學術上,特克在本書探討行動裝置所帶來更加複雜的人際連結樣態時,實際上呼應了約莫是2002年以後傳播與媒介研究的主要觀點。另一方面,在一個更廣的社會文化脈絡上,我們可以說《在一起孤獨》這本書談的正是我們這個時代鬱積已久的病徵。
為何我們對科技的期望日漸增高,卻對彼此的期待日漸降低?(資料照,圖/CurrencyFair @ flickr)
ames Katz與Mark Aakhus在2002年編著了一本後來被認為是行動通訊研究的重要論文選集。這本書的主標題是:永恆聯繫(perpetual contact),它一語道出了行動裝置普及帶來的影響,也成了其後十數年間影響許多研究的重要理論概念。簡言之,「永恆聯繫」指的是:由於行動裝置隨身攜帶、即時連結的科技特性,人們如今實實在在地進入了一種「不斷線」的狀態。過去,我曾將桌上電腦的網路漫遊者稱為「脫殼之人」,也就是一種擺脫固著於當下的肉身、躍入「螢幕生活」中的抽離樣貌。這種看似無遠弗屆的連結,實則需要以固著的肉身為代價。因而,一但身體移動、離開那閃爍的螢幕,連結也就跟著中斷。但行動裝置內蘊的永恆聯繫卻是全然不同。幾乎不再需要電源線、網路線的手機、平板電腦,讓我們如今無需「脫殼」躍入螢幕。我們把螢幕生活就這樣放在口袋裡帶著走。
特克在《在一起孤獨》書中所探討的人際連結樣態,其核心正是這種「永恆聯繫」。她更進一步指出這種「永不斷線」帶來了新的自我狀態,一種拴上連結的自我(a tethered self)。此狀態呈現出今天我們自身相當熟悉的一些問題。例如,拴上連結的自我意味的是,時時刻刻都有那麼一條連結,會將你我抽離當下環境。我們應該都很熟悉這樣的情境:隨著手機鈴響,自己就這樣被前一秒正在聊天的朋友「暫停」。又或者,你大概也被迫參與過公車鄰座乘客與其另一半吵架的過程。換言之,拴上連結的自我狀態,也就是一種需時時刻刻面對並處理「雙面舞台」的處境(物理在場與虛擬線上)。但就如特克不禁質疑:「如果身體在場的人心在別處,地方還算是地方嗎?」其他關注相同現象的學者也曾批判地指出,這可說是一種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失控發展。也就是說,透過行動裝置進行連結的個人,就好像在與他人共同在場的空間中,私自地築起了一道圍籬。
拴上連結的自我狀態不僅凸顯出今天我們面臨的公/私界線模糊問題,特克還點出了另一個更重要的現象:持續分心的世界的到來。關於「注意力」在這個數位時代成為稀缺資源這件事,讀者們應該都很熟悉了。如果用我在上文提到的「雙面舞台」概念做進一步說明,持續分心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我們需要同時間處理好幾個舞台演出的狀態。每一個舞台發生的事情都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都要求我們的關注與回應。在受限於一具身體的物理條件下,我們只有兩種行動可能:選擇專注於某一個舞台,或者選擇快速地在不同舞台間切換──也就是持續分心。
在數位時代前,專注也許被視為是一種好的習慣、能力,但今天我們越來越常看到許多人反而在談論「分心」作為一種技能的好處。例如,紐約時報知名記者尼克.比爾頓在《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中,就認為今天已是「多工族世代」。著有《虛擬社區》、《聰明行動族》等重要著作的網路研究者霍華德.瑞格德,也在其前幾年出版的新書《聰明網路使用手冊》中,談論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如何是重要的數位技能。
然而,對於特克來說,持續分心現象背後的意義卻不只是如此。除了談到在這樣的世界中,我們已逐漸跟不上科技為我們設定的生活步調外,更深層的是,她看到了人自身在這樣過程中所經歷的化約。特克指出:「連線的生活鼓勵我們用類似處理物品的方式,迅捷有效地對待我們在線上遇到的人」。至於線下的人呢?則都變成是「可暫停的」(pauseable),面對面的互動不斷地被來電與簡訊打斷。
(相關報導:
短短三年,世界天翻地覆:《謝謝你遲到了》選摘(3)
|
更多文章
)
雖然特克沒有進一步討論,但這種將他人視為物品、可暫停的狀態,直接地讓人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於現代科技的批判。海德格認為,現代科技的作用是將自然萬物原有的豐厚意義化約為僅供人使用的資源。同時他也警告,雖然看起來人在其中好像是主宰、支配者,但實際上人也將變成同樣化約的存在。過去我們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將人降格為人力資源時,其實就呼應著海德格的預言。如今,特克的觀察顯示出,不僅在生產勞動體系,在日常的互動生活中,人也被化約為某種近似物的狀態,可供彼此瀏覽、暫停與即時取用。
由此看來,不同於比爾頓與瑞格德,特克是以較為批判的角度看待持續分心世界的到來。對她來說,持續分心的狀態也許沒有那麼美好,相反地,它從根本上危及了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甚至可以說,《在一起孤獨》全書所透露出的確實是相對悲觀的論調。特克自己在本書最開端處也是如此自陳。不過,我們稍後再回來討論這個問題,先讓我繼續說明第二個脈絡。
閱讀《在一起孤獨》的第二個脈絡是,我們可以在特克厚實的敘事中看到這個時代鬱積已久的病徵。
特克的每一位訪談者說的,好像都是我們自身的故事。明明就坐在附近的同事,卻總是用簡訊傳話。多數的時候,我們選擇用即時訊息取代打電話。用十七歲的伊蓮的話說:「好多人都對電話深惡痛絕」──就算不是如此誇張,電話如今也成了完全陌生或極為親密關係的限定物。但同時,我們卻再也離不開手機、網路。「永不斷線」不僅是一種客觀狀態,更是如今人們感到安心的保證。
這是一種矛盾的人際關係樣態。我們看起來好像不想與他人靠得太近,因此盡量避免使用過於「親密」的媒介(也就是打電話)來聯繫彼此。但我們又看起來不想獨處,無論何時何地都得盯著手機螢幕上的朋友們。於是,簡訊、即時通訊這類因其文字介面而讓人們得以「保持距離」地在一起的媒介大行其道。這不僅是因為簡訊、即時訊息讓人可以更輕鬆地整飭自身的形象,更是因為它們似乎可以用來緩解這個時代人對於親密關係既愛且恨的正負情愫。
用英國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的話來說,這種矛盾情愫可以說是「解放」的代價。這裡所謂的「解放」,指的是進入現代社會後,人們從傳統諸多僵固的限制掙脫的過程。除了傳統的規範、權威開始瓦解外,一個很重要的轉變是人際關係紐帶的鬆動。人與人的關係不再如過去那般固定、沉重,不僅在對象上我們有更多自由的選擇,各種運輸、通訊科技的普及,也讓過去限定人際關係的僵固時空框架軟化。用包曼的譬喻來說,我們的親密關係「液態化」了。
然而,解放、擁有更多選擇自由、更彈性的人際距離,這些看似美好的處境,其實不全然都是好的。包曼在其一本著作《自由》中便指出,實際上,「自由的需求和社會交往的需要──儘管它們經常摩擦,但無法分割──似乎是人類自身狀況的一個永久性的特徵。」換言之,只有「自由」是不足夠的,人恆常也有著與人建立親密交往關係的安全需求。但就如同你我都可能曾經歷過的,過於緊密的關係卻反過來又將使自由窒息。於是,不同於傳統社會中人們生活在緊密的共同體,「解放」的代價就是我們今天必然要面對著自由與安全的矛盾需求、愛恨交織。
(相關報導:
短短三年,世界天翻地覆:《謝謝你遲到了》選摘(3)
|
更多文章
)
特克雖然沒有點明這樣的脈絡,但其書名的「在一起孤獨」卻絕非巧合地對應了自由與安全的矛盾。從《虛擬化身》開始,特克就已看到自我認同如何在模擬現實中隨意變形。十數年後,在觀察行動裝置帶來的轉變中,特克更清楚地指認出我們已然「液態化」的人際關係。然而,透過行動裝置、簡訊、社群媒體等媒介緩解液態化人際關係帶來的焦慮,並非治本之法。在前一節,我們已經指出,對於特克來說,這種想要透過科技兼得魚與熊掌的做法,最終導致的反而是人與人的關係、甚至人自身的化約。談到這裡,是時候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特克的悲觀論調。
只靠視訊,其實彌補不了見不到面所流失的情感。(資料照,圖/河村友歌@PAKUTASO)
特克在本書最初〈作者的話:轉捩點〉中有一句話最能體現她的悲觀:「我讓我的故事停在一個令人不安的對稱上:我們似乎決定要賦予物人性,並滿足於把彼此當作事物來對待」。換言之,我們可以說特克憂慮的核心,源自於人與科技物的親密關係。這樣的親密關係看似帶來美好、便利的生活,實則是悄悄地改變了「人」的意義。
但是,人的意義的改變,這本身不必然是件壞事。顯然地,特克的憂慮來自於她從一種浪漫懷舊的立場想像人自身。例如,在談到與機器人的互動關係時,她指出,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變化,是過去人們重視的人所獨有的那種情緒、情感性的「浪漫反應」,在如今這個機器人時代中,一切都是資訊至上。過去那專屬於人的「神聖」特質,如今已不再那麼重要。又或者,她在談到社交機器人作為伴侶逐漸成真的未來,也認為這是一種關係的簡化、貶低,在其中人喪失了學習進入並維持複雜關係的能力。因為機器人在她看來只是一種「自體客體」(selfobjects),只是個人需求、脆弱內在的投射,缺乏真正異己主體的反應能力。
特克的悲觀、憂慮當然不全是杞人憂天。無論何時,我們確實都需要警醒科技帶來的化約作用。但是,晚近諸多關於賽伯格與後人類處境的討論也顯示,我們仍然可以積極地看待、思索人與科技物歷經的這一親密轉換。一方面,行動裝置、社群媒體的永恆連結,不只有導致關係的化約、人的物化。如果從賽伯格的角度來看,人與行動裝置的親密結合作為一種延伸認知系統,我們確實有了跨越時空藩籬看見、聽到並共同感受的可能。進而,這種共同感受、回應的情緒,雖然不同於傳統社群紐帶,卻也開啟了共同生活的另類選擇。換言之,套用技術哲學家Don Ihde的說法,科技所帶來的影響始終都有著擴增與化約兩個正反並存的面向。我們需要警覺特克那令人不安的對稱,但也仍需積極地探問如何與科技更好地共生下去。
另一方面,對於人與科技物親密關係的反省,也不必然要從對人的懷舊出發。特別是當我們從Donna Haraway的賽伯格隱喻來看,人與科技物的親密關係反而能夠讓我們進一步反思「界線」的問題。這裡所謂的界線問題,指的是在過去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下,「人」一直被是為獨特的主體。就如同有一條不可踰越的線,區分出理性、具情感性、有行動能力的人類主體,與另一邊無意識、情感也無行動能力的客體。這條界線可以說是現代社會得以建立的根基,在此之上,我們不僅正當化了人對於自然萬物的宰制、剝削,也正當化了其他界線──例如,更理性、更具行動力的男人,與另一端「不足夠」的女人。人與科技物的親密關係、越來越「像人」的人工智慧、越來越「機器化」的人類工作者,這些種種現象質疑了上述鞏固著現代性神話的界線。換言之,如果人不再、或甚至從未獨特,如果那條不可踰越的線實際上是由人自身所建構,那麼我們是否能嘗試打破並重新打造界線,並藉此探索人與非人、男人與女人、或者各種僅僅具有平凡差異的物種的共生之道?
總之,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人的處境。現在,我們全都是賽伯格。賽伯格不是科技浪漫主義中的「超人」(trans-human),但它也不見得如特克憂慮的那般,只會導致人自身以及人與人關係的貶抑。雖然《在一起孤獨》帶著較為悲觀的論調,想要警告我們正輕忽著數位科技發展潛藏的危險。但我相信這並不是最終章,對於特克來說,三部曲也絕非完結。就在去年年底,特克又出版了一本新書《重啟對話》(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顯然地,她試圖延續《在一起孤獨》的討論,並積極地尋找出路。而現在,我們也可以開始閱讀這本書,並思索著自身的答案。
(相關報導:
短短三年,世界天翻地覆:《謝謝你遲到了》選摘(3)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在一起孤獨》一書,本文為推荐序,作者為輔大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本書作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現居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科技社會研究教授,MIT科技和自我創新計畫(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創辦人兼主任,也是有執照的臨床心理學家。投身科技心理研究超過三十年,被凱文.凱利譽為科技界的佛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