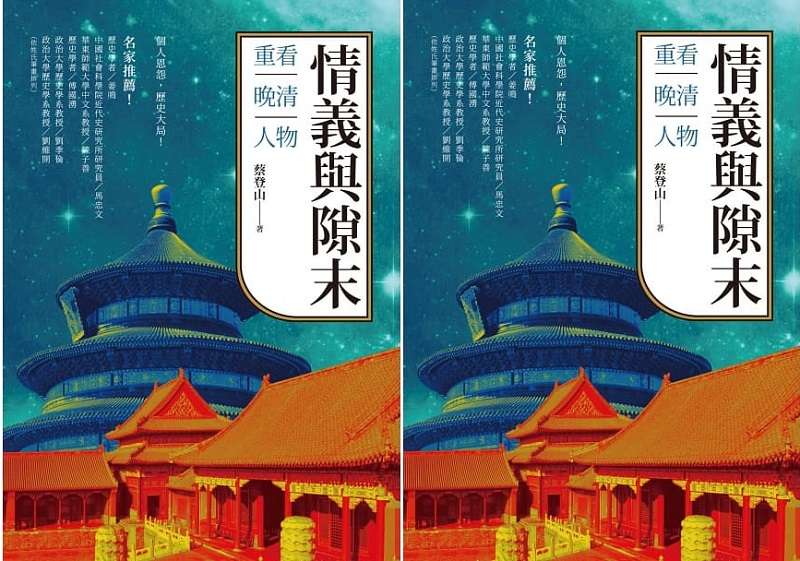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終激盪著兩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漸傳入中國,所謂「西學東漸」;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也逐漸走向世界,所謂「中學西漸」。在這交流之中,翻譯成為不可或缺的樞紐工作。我們看晚近的翻譯史上,由西書中譯者可說相當多,例如嚴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嚴譯名著」影響到幾代的中國人;而單就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實秋、孫大雨、卞之琳等等名家卓越的譯品;但若就中書西譯方面就顯得貧乏許多,但後者的意義顯得更來得重要些,它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工作。而要能擔當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抵要極其深厚,而非只是語言能力足夠就行,因此辜鴻銘就曾被視為是近代中學西漸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可以當之。
辜鴻銘這位滿清遺老在一九二八年風雨飄搖中死去,他的辮子、他的守舊,逐漸為人所淡忘;但他所譯的《論語》、《中庸》被介紹到西方去,再加上他的西文著作,曾引起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及舉世公認的文評家勃蘭兌斯(Brands)的重視。而林語堂更是沒有接受魯迅的建議去翻譯一些英國名著;他反而懷抱著「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雄心壯志,做起中書西譯的工作,他早年曾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但後來考慮再三,覺得它距離現實太遠,因此他借鑑了《紅樓夢》的藝術形式,用英文寫出了長篇小說《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它曾是諾貝爾文學獎候選的作品。
但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林語堂終究還是完成耗時十餘年的《紅樓夢》節譯本,惜未能出版(案:據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宋丹博士表示林語堂英文打字稿,現存於日本某家市立圖書館,林語堂將《紅樓夢》的書名譯為《The Red Chamber Dream》。書名下印著「A Novel of a Chinese Family」(一部中國家族的小說)原稿共859頁,包括林語堂的解說、序章以及作為主體的六十四章和終章,是對《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編譯。)
林語堂耗時十餘年完成《紅樓夢》節譯本,卻未能出版。(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一九八四年有日本佐藤亮一根據林語堂的英譯本譯成日譯本。而之後他又以英文出版了《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全面向外面人介紹儒家及老莊的思想,在在引起國際上的關注。當然在譯書之前,林語堂以英文撰寫《吾國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與《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成為歐美暢銷書排行榜的年度冠軍。《吾國吾民》與《生活的藝術》成為當時西方社會眺望中國的一扇窗口,林語堂扮演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這個角色,無疑地是極其重要的,它成為林語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貢獻。
陳季同(1852-1907),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他十六歲時考入福建船政局附設的求是堂藝局前學堂讀書。學堂的教師多為法國人,用法語講課,所用的教材也是法文書,因此陳季同在此打下了紮實的法文基礎。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初,船政第一屆學生畢業。陳季同與魏瀚、劉步蟾、林泰曾等人,以「在學堂多年,西學最優」,被船政局錄用。同年三月隨法人日意格赴歐洲採購機器,遊歷英、法、德、奧四國。一年後返國,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三月三十日,福建船政局選派三十五名學生從福州啟程赴歐洲學習,其中有後來成為著名人物的嚴復、馬建忠、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薩鎮冰等人。
陳季同集翻譯家、西文作家、詩人和文化使者於一身。(資料照,作者提供)
而陳季同在這次赴歐時的身份,已提升為文案,遠較這批留學生高出許多。到法國後,陳季同進入法國政治學堂(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及法律學堂(Ecole de droit),學習公法律例。光緒四年(一八七八)陳季同充當中國首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的法文翻譯,郭嵩燾對年輕的陳季同評價甚高,他認為陳「再經歷練官場,中外貫通,可勝大任矣」。而陳季同果然沒有讓郭嵩燾失望,幾年之後,他在外交界就嶄露頭角了。當時亨利‧比盧瓦(Henri Bryois)就曾在《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說:「在他之前,中國使館形同虛設,僅僅充當一個拖著長辮、身穿藍袍、頭皮光光的大人物的住宅。從外交角度坦率地說,因為有了這個年輕翻譯的活動,中國才開始在歐洲嶄露頭角。」
陳季同在歐洲共居住了十六年,他的成就不僅體現在外交上,更體現在文化上。但可惜得是陳季同的事蹟正史不載,辭書不收,就這樣被歷史遺忘將近一個世紀,直到十幾年前才有學者論及。而大陸學者李華川博士更曾遠赴法國查遍外交部檔案及巴黎的圖書館,以三年的時間寫就了《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一書,於二〇〇四年八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全面評價陳季同的開始。據李華川的蒐集陳季同有八本法文的著作,分別是:1、《中國人自畫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2、《中國人的戲劇》(Le theatre des Chinois),3、《中國故事集》(Les contes Chinois),4、《中國的娛樂》(Les plaisirs en Chine),5、《黃衫客傳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6、《巴黎人》(Les Parisiens peints par un Chinois),7、《吾國》(Mon pays),8、《英勇的愛》(Lamour heroique)。而這些著作還有英、德、意、西、丹麥等多種文字的譯本。李華川認為在清末的文人中,沒有人比陳季同在西方更引人注目。
其中《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的娛樂》兩書,在西方影響尤大,甚至都被譯為英文,就如同半個世紀後林語堂的《吾國吾民》與《生活的藝術》所產生的影響一般。陳季同寫這兩本書的目的是要讓西方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的生活、習俗和娛樂,從而更好地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前者他以生動而富有情趣地描述中國社會有關政治、經濟、宗教、教育、文學等各個側面。後者則是從娛樂的視角:遊戲、儀式、節慶,來描述中國。
(相關報導:
中國無聲入侵,沒有民主國家有這樣全球投資的想像:《妖風》選摘(3)
|
更多文章
)
在一百多年前陳季同已意識到:不同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社會規範是不同社會價值觀的真實寫照,而不同社會又具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和社會期望;由其間的差異性所造成文化碰撞,文化衝突,交際失誤產生的後果也往往是十分嚴重的。他的批評雖有批評中國傳統習俗,但更多是針對西方。他說:書中「對西方風俗習慣的批評隨處可見。千萬別忘了我寫作時用的是鋼筆,而不是中國的毛筆,並且我已經學會了按歐洲人的方式來思考和寫作。」
而對於《中國人的戲劇》一書,李華川認為是中國人以西方方式論述中國戲劇的第一部著作。陳季同觸及中西戲劇中一些本質的問題,可說是相當精闢的。他認為中國戲劇是大眾化的平民藝術,不是西方那種達官顯貴附庸風雅的藝術。在表現方式上,中國戲劇是「虛化」的,能給觀眾極大的幻想空間,西方戲劇則較為寫實。在布景上,中國戲劇非常簡單,甚至沒有固定的劇場,西方戲劇布景則盡力追求真實,舞台相當豪華,劇院規模很大。
《中國故事集》是陳季同的譯著,他選譯《聊齋誌異》中的26篇故事,並改譯原有的篇名,而代之較為西化的篇名(例如將〈畫皮〉改為〈吸血鬼〉,〈聶小倩〉改為〈神奇的盒子〉),其次對原文也作了刪節,簡化了原本複雜的敘述,它成為《聊齋》最早的法譯本,也引起較大的關注,法國名作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都曾為他寫書評。
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名作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曾為陳季同所著的《聊齋》法譯本《中國故事集》撰寫書評。(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黃衫客傳奇》是陳季同的長篇小說創作,它雖是取材於唐代蔣防的《霍小玉傳》,但《霍小玉傳》只有四千餘字,《黃衫客傳奇》卻寫成一本三百多頁的長篇小說。它是一部現代意義的歐式小說,它與中國傳統小說迥然有別,這在陳季同之前,似乎還沒有人做過類似的嘗試。
《吾國》是陳季同輯錄一八九二年以前在歐洲撰寫的單篇文章而成的集子,而《巴黎人》則是他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去看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並加以評論。至於《英勇的愛》是陳季同已回到中國後創作和出版的法文劇本,他曾熟讀法國戲劇大師莫里哀的作品,自稱「莫里哀的弟子」,又受到法國劇作家拉比什「輕喜劇」的影響,《英勇的愛》是一部獨幕輕喜劇,共分九場。作者全盤打破中國傳統戲劇以演唱為主的表演模式,代之以西方話劇的對白形式。
學者錢林森對於陳季同有極為深刻的評價,他說:「做為中國文化和文學的闡釋者,做為中西交通最初的溝通者,陳季同的創造最具價值的部分,不是他直面西方文化時所流露的自豪、甚至自誇的情愫,而是他正視西方文化時所擁有的比較意識(如《中國人的戲劇》)、自省意識(如《巴黎人》),以及在移譯、闡述、運用中國文學和文化時所表現的現代意識、創造意識和世界眼光(如《中國人的戲劇》、《中國故事集》、《黃衫客傳奇》、《英勇的愛》)。他在這方面的嘗試和實踐,無疑又擔承著一個先行者的角色,並取得了成功。⋯⋯當時法國文壇的領軍人物法朗士等,便是通過陳季同和他的作品一窺中國文化的。」
「十幾年致力於讓歐洲認識中國」的陳季同,卻以私債風波把他的成果毀於一旦,使他在外交界的努力化為泡影,他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以代罪之身回到中國。後得李鴻章的庇護,在清償債務後,留在李鴻章幕府中襄助洋務文案。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割臺時,陳季同曾於同年五月十四日抵臺,他原本是奉李鴻章之命為其子李經方交割臺灣給日本做準備的,但他耳聞目睹臺灣人的誓死抗日,他卻站到臺灣老百姓的這一邊。
(相關報導:
中國無聲入侵,沒有民主國家有這樣全球投資的想像:《妖風》選摘(3)
|
更多文章
)
王松《臺陽詩話》說:「乙未,臺灣改立民主國,即陳季同先生所建議也。」他當時是仿效法國的民主政體,為臺灣紳民拒奉朝廷割地之命尋求一合理解釋。他為尋求法國的支持,還登上法國軍艦,向法國政府送交相關信函。五月二十五日「臺灣民主國」正式成立,連橫在《臺灣詩乘》中說:「乙未之役,臺灣自主,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以禮部主事李秉瑞為軍務大臣、刑部主事俞明震為內務大臣、副將陳季同為外務大臣。」只是臺灣的軍力無法抵擋日本的重兵,最後唐景崧等官員內渡,民主國也為之煙消雲散了。
著名的小說家和翻譯家,同時也自稱是陳季同的學生的曾樸說:「回國後,李鴻章極器重他,屢次派往外洋,官至總兵。後來因事件忤了鴻章,就退居上海,過他文人浪漫的生活。先生不獨長於法文,中文也極有根底,尤其是詩歌;性情質直而熱烈,不受羈勒;晚年頗染頹唐色彩,醇酒婦人中,往往作狂草,唱悲歌。」
清朝短暫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即為陳季同所建議,當時陳季同仿效法國的民主政體,並積極尋求法國的支持。圖為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摹繪本。(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之後,陳季同在上海首先參與創建中國女學堂,後又創辦《求是報》(International Review)。此時他的主要工作轉向中國知識界傳播西學。他在《求是報》中翻譯、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和法律、政治制度,宣傳了維新思想,傳播了西方的政治、法律觀念。他是最早翻譯《拿破崙法典》的,因為他精通法國的政治律法,「雖其國之律師學士號稱老宿者莫能難」。即便晚年閒居滬上,「西人有詞獄,領事不能決,咸取質焉;為發一言或書數語與之,讞無不定。其精於西律之驗如此。」
陳季同在當時就很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文化不應故步自封,應該走向世界,他說:「我們在這個時代,不但科學非奮力前進,不能競存,就是文學,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為獨一無二的文學之邦。⋯⋯我在法國最久,法國人也接觸得最多,往往聽到他們對中國的論調,活活把你氣死。」其所以會如此,他認為「一是我們太不注意宣傳,文學的作品,譯出去的很少,譯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譯得不好,因此生出種種隔膜;二是我們文學注重的範圍,和他們不同,我們只守定詩古文詞幾種體格,做發抒思想情緒的正鵠,領域很狹,而他們重視的如小說戲劇。我們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誤會。」
他不遺餘力地向西方宣傳文化,其用意在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讓中國能夠融入世界。他曾向曾樸談過如何消除中西文化的隔膜和誤會,他說我們首先應確立「不要局限於一國的文學,囂然自足,該推擴而參加世界的文學」的態度,然後「要參加世界的文學,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翻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須全譯出去!要免誤會,非把我們文學上相傳的習慣改革不可,不但成見要破除,連方式都要變換,以求一致,然要實現這兩種主意的總關鍵,卻全在乎多讀他們的書。」
這種國際的眼光在當時可說是領先於許多知識份子的。當然它對於曾樸的走上研究、翻譯法國文學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未來的三十餘年中,曾樸翻譯法國文學作品約有五十多種,他也始終未曾忘懷陳季同這位他的法國文學的啟蒙老師。
曾樸翻譯大量法國文學作品,期啟蒙老師即為陳季同。(資料照,作者提供)
曾樸在給胡適的信中追述陳季同說:「我自從認識了他,天天不斷地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藝復興的關係,古典和浪漫的區別,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由進展的趨勢;古典派中,他教我讀拉勃來的《巨人傳》,龍沙爾的詩,拉星和莫里哀的悲喜劇,白羅瓦的《詩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論;浪漫派中,他教我服爾德的歷史,盧梭的論文,囂俄的小說,威尼的詩,大仲馬的戲劇,米顯雷的歷史;自然派裡,他教我讀弗勞貝,佐拉,莫泊桑的小說,李爾的詩,小仲馬的戲劇,泰恩的批評;一直到近代的白倫內甸《文學史》,和杜丹,蒲爾善,佛朗士,陸悌的作品;又指點我法譯本的意、西、英、德各國的作家名著。」可見其國際視野的眼光,在那個年代誠屬不可多得,也難怪曾樸讚其為中國「研究法國文學的第一人」。
今天臺灣的國中生在歷史課本的臺灣史部分,都可以讀到在臺灣民主國建立中,占有重要位子的臺灣布政使陳季同的名字。但是除了這一小段和臺灣有關的事蹟外,大家對陳季同的成就與貢獻,可說是茫然無知了。一個百年前傑出的文化使者,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驅者,是不該再讓他湮沒無聞的,在他的法文著作陸續翻譯出版的今天,也是我們重新認識他的時候了。久違了,陳季同先生。
(相關報導:
中國無聲入侵,沒有民主國家有這樣全球投資的想像:《妖風》選摘(3)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等數十本著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情義與隙末:重看晚清人物》(新銳文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