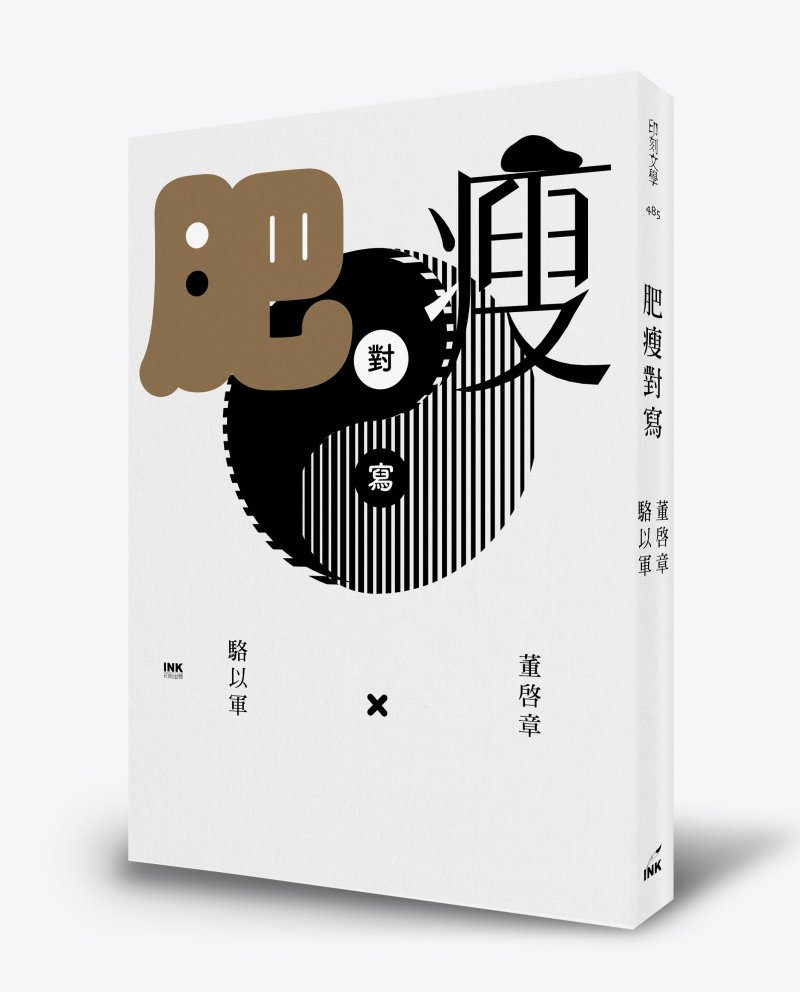同為一九六七年生,台港兩位作家駱以寫、董啟章以一年書信往返,筆談創作途中風景,困頓常多於歡愉,彷如在各自的荒墟探險之夢中尋找出口又是自難自苦地更深入,並對這時代整體遭棄廢墟般的失重荒蕪感的持續總體檢。文中,「瘦」的是董,「肥」的是駱,不論肥瘦,他們以沈靜的文字,為彼此的孤獨療癒。
瘦:
在這許多公路電影中,我特喜歡那部俄國導演Andrey Zvyagintsev的《歸鄉》:謎一般的父親,突然出現在這兩男孩的世界,並帶他們展開一段荒涼、詩意、整個世界那麼暴力、絕望而他們得上路的旅程。那父親隱喻了所有「父親陪孩子上學途中」的形象:寡言;不擅長隱藏感情;因為被小孩並不知道的這個世界傷害過了而呈現一種線條的剛硬;不理會小動物似的軟軟的在路途中因好奇而耽擱、分心;以軍事化的粗暴訓練這兩兄弟獨立(讓還是小孩子的他們,學習開車、划船、對付對他們粗暴的青少年、如何面對曠野孤獨的恐懼)。兩個男孩恨透了這個憑空冒出的父。但最後怪異的,他們在那無人的小島上意外地害死了這個父親,他們─一個奇怪的迴圈一恰用那父親一路暴力施加強迫他們學習的技能:用棕櫚葉拖父親的屍體、替小船塗上瀝青以防水,成為孤兒的兩人疲憊地在大海上操槳划舟,終於回到了最初的碼頭,那載著父親屍體的小船又沉入大海。這個父從虛空中闖出,又像從無這個人的回到虛空。兩兄弟瞬間成為大人的心智,開著父親遺留的那輛爛車(以及他教給他們的技能),將那公路陌生之境轉為「歸途」。
這事我覺得九年了(先是我大兒子,後來是兩個孩子一起,現在是小兒子),我幾乎每日早晨得送孩子到他們小學後門,或下午到同一地點等候,帶他們回家的這段路,可能不到三百公尺吧。就是穿過一些公寓和日式魚鱗瓦老屋、樹木的綠蔭密覆的巷弄,比較特別的是會經過新生南路一座清真寺的背後、緊鄰著一間天主堂,到那條巷道的底端,有一間香火算鼎盛的小媽祖廟,神龕上黑臉女神鳳冠霞帔,侍將猙獰,但其實經過時,裡面總有一些老人汗衫短褲拖鞋坐摺疊椅在車馬炮對賭。這段路總讓我擔心,太平靜無有驚奇,太安全了。
(相關報導:
揭開墨的漆黑面紗:《墨客列傳》選摘 (1)
|
更多文章
)
比起我小時候住永和,換過三所小學,但上學放學之途,無不像一趟小規模的冒險,長征,沒有大人陪,穿過那迷宮般,十二指腸的巷弄,快步走至少要十五至三十分鐘。途中經過車潮洶湧的馬路,可見殺雞宰魚場景的傳統市場會有小巷裡讓你流連忘返的柑仔店,那些琳琅繁花般的五角抽,或那麼一台賭博性的水果盤機台,有彈子房(那更是會衝出勒索你的邪氣青少年),有工地,我們會翻進那些拆除到一半的鬼屋般的日式老宅廢墟,穿梭冒險,有的走河堤,用石子投擲樹梢的木瓜,或闖進一座吊了七八塑膠袋貓屍骸的竹林,較大一點後(約國一到國二),我的同伴還幹過偷腳踏車的壞事,推著偷來的腳踏車到學校附近的修車行換煞車或補胎,小鬼就可以對那一身黑油總是蹲著的老師傅沒大沒小殺價……
小時候上學放學之途,無不像一趟小規模的冒險,長征,沒有大人陪,穿過那迷宮般,十二指腸的巷弄,快步走至少要十五至三十分鐘。(圖/挪威 企鵝@flickr)
我還曾經撞見一個小廟拜拜之前的辦桌(吧),一群老人圍著,其中一人用尖刀殺一隻豬,那是個冬日清晨,所以我印象中從豬被割開的喉管,或他們往那還在微弱掙扎睜著黑眼睛的畜生身上淋澆滾水,都不斷冒出蒸騰的白煙。
這些活跳跳「上學途中所見」時刻,我父親從不在那畫面陪在童年的我身邊。我是不是希望將我想像的、期望的(也許是陌生的驚嚇或恐怖、超出一個小孩能理解的豔異之景),塞進我孩子的上學途中?但是否我總陪在身旁,那冒險的、危險的時刻、那意外誤闖的暗巷歧路,便總不會真的對他們展開?
啟章,和你聊這個話題,我特別有感覺。我們是同代人,不覺也各自走到這個年紀。你的長篇,特別給我印象畫派《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給新新人類》這樣的負軛、贖回、啟蒙的未來小說大全景的意念。好像是我們不覺也走在這個世界的夢境或街景。
近半世紀啦,我們也許從年輕時的「歪斜人」,孤種的《安卓珍尼》,從裡面長出一個「父」的身分,守護者(如此脆弱)或更是陪伴者(如此驚懼或哀傷)。
我曾聽你說過,你帶阿果上學的路途,比我艱難許多(印象中換乘火車、巴士,種種不同交通工具)。父與子在(香港)那樣街車人潮中的前進。對我而言就像極小規模的公路電影。
不可預期的,慢慢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我或是你在那段不進入路程,但其實累加起來漫漫長途的「上學途中」,長出了一個內在安靜、無人知曉的什麼小宇宙?
孩子的位置放在哪裡?或跟在一旁走的你(父親)在哪個「觀看人類全景」的位置?───肥。
肥:
老實說,接送兒子上下學的途中,我多次想逃掉。
或者,說真的啦,也不是真的逃跑(因為實在跑不到哪),而是渴望這樣的生涯早早結束。
從孩子上小學開始,就要從新界北區送他到九龍市區上學,因為他不像一般小孩本區就讀,而是選了家比較遠的學校。但說遠也不是真的很遠,如果坐火車的話,半小時就到,加上步行距離,頂多是四十五分鐘。還可以的。問題是,兒子的特異嗜好,或直接點說,怪癖。
坐火車,我兒子是絕對不肯坐「舊款」的,也即是舊的型號,準確地說是英國製的都城嘉慕列車,從鐵路轉為電動化的一九八二年服務至今,期間車廂經過翻新。他要坐的是「新款」,也即是日本製的近畿川崎SP1900列車,一九九九年投入服務。兩種車又簡稱為「圓頭」和「尖頭」。問題是,新款或尖頭全線總共只有八列,而舊款或圓頭卻有二十九列。八比二十九,結果可想而知。每天上下學坐火車,就是一場大賭博。好運氣的,等三或四班之內坐到;倒楣的,十班也等不到,或更可怕的,跑到月台剛剛送車尾。那是令他(以至於我)崩潰的事情。
常常因此而要提早很多出門,也常常因此而兩父子在月台或車廂內大動干戈。我兒子的反應我就不詳細描述了,總之就是固執如石,橫蠻如牛,天地都不怕,全世界照罵。簡單地說,就是無法理解和接受世事無常,世界不是順應他的意思。而從他三歲開始出現超級分別心和固執狂,我作為父親就已經無法以權威甚或暴力鎮壓(試過硬把小小的他拉到車上結果全程哭鬧直至你厚不住臉皮在下一站下車),又或者各種計分獎賞溫柔讚美的方法,去緩解他對於沒有規律的事情的焦慮和恐慌。而解釋世界為何不按個人意願運作,所謂好壞只屬主觀並無實質,或者人生就是要面對不如意等等的大小道理,多年來天天說也說上了過萬遍。但是,他沒有絲毫動搖。
看著孩子沒法像其他正常人一樣坐車,甚至為此而毀掉了一整天的心情,無法好好上學,心裡真是莫名其妙的悲痛。好像不是什麼的大事吧,但是,這只是同一思維(或情緒)模式的其中一個例子。基本上這就是他經驗人生的模式。我也曾說過,如果你能夠安然愉快地等,爸爸可以忍受,可以陪你等下去,這個「不正常」是沒關係的,但是,千萬別發脾氣,怪別人。有時他可以做到一下,但很快又不行。而制止他無理暴怒的最後手段,就是比他更暴怒,發飆得更厲害,非如此不可鎮住他的情緒。讓他也覺得我太過分了,他才有點畏怯的稍歇一下。不只一次,我就像個精神病漢一樣在眾目睽睽下大呼小叫。我想,我也變得有點「不正常」了。
當然,在好運的日子,會看到他像其他孩子一樣乖乖地坐車,一臉安靜滿足的樣子。或者在下車之後,還站在月台上依依不捨地看著心愛的列車離去,或者興奮地和我說著不同型號之間的車頭燈的分別或各種諸如列車號碼編排之類的精細而無用的知識。這些時刻我就不禁想,如果這是他偏執的人生中的唯一快樂,我又怎忍心把它滅掉呢?
今年孩子小六了,這個學期他開始自己上下學了,而我也終於如願結束忍受多年的迎送生涯。除了多一點自己的時間,也可以不用再面對那些令人腦袋癱瘓無法即場應對的驚嚇場面了。可是,其實兒子還是要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而我,竟然已經開始懷念每天帶孩子坐火車上下學的日子了。────瘦。
*本文選自印刻文學出版的《肥瘦對寫》,作者為駱以軍、董啟章。駱以軍(代稱:肥、胖)一九六七年生於台北。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專職作家;董啟章(代稱:瘦)一九六七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於書內,兩位作家分別以代號「肥、瘦」進行交談。
(相關報導:
揭開墨的漆黑面紗:《墨客列傳》選摘 (1)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