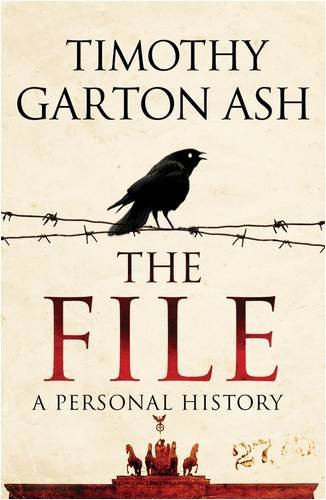據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未來的歷史。這句話簡單直接,似乎大家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甚至還能同意。但只要稍稍一想,就會發現這句話其實問題重重。例如,它似乎隱含了一個標準,一個什麼事情能被寫進歷史的標準;難道只有今天被新聞媒體報導過的事實才夠得上歷史的殿堂嗎?當然不,因為我們在報導新聞的時候,在判斷什麼事情才有新聞價值的時候,總是已經先有了一套預設,而這個預設又總是離不開我們這個時代的視界;明天的史學家憑什麼要全盤接受我們這個時代的視界呢?此所以重大的史學進展往往和新史料的發掘相關;那並不只是新發現了一批被人遺忘的文檔那麼簡單,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從未想過要入檔留存的東西當成史料。比方說樹木的年輪,前人可曾覺得這是訴說他們那個時代事實的重要線索嗎?可今天的史家已能學會在一片樹林的年輪裡判讀過去氣候變化的痕跡,從而掌握往昔人們生活勞作背後的自然條件。所以我們不妨大膽地說,今天的新聞固然可以是未來的歷史,但對今日新聞標準的疑問更有可能是未來歷史學者的重點。
事實,乃是現代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只是事實如何發掘,更是事實到底可以證明什麼的問題。自從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種忽略事實與證明之關係,轉而強調事實被詮釋被敘述的傾向(或者可以叫做後現代傾向),就漸漸又變成史學主流的趨勢了。因為什麼算是史料,什麼叫做事實,基本上是個看你把它們放在什麼框架之下敘說,又如何敘說它們的問題。畢竟,任何時代的人用以了解他們那個時代的視界及價值標準,都是一些可以說出來的敘事,並且還可以不斷重新敘說。所以今天當我們在談歷史的時候,講「故事」、「敘述」和「書寫」乃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幾乎恨不得把歷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說似的純粹敘述技藝。相反,依舊堅守某種單純甚至天真的事實之力量,則是不合時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實即顛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書,因為它連書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書序言裡所講的,他依然相信「事實具有顛覆性,能夠推翻民選領導人和獨裁者、傳記作家和自傳作者、間諜和英雄、拷問官和後現代主義者的斷言,能夠推翻謊言、半真半假的東西和神話,能夠推翻所有『為了安慰悲慘之人而脫口而出的演講』」。這是真的嗎?事實本身就具有這樣的顛覆性嗎?還是說編纂事實和安排事實的新敘事使得事實顛覆?
賈頓艾許在英語世界和歐洲可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當過英國《觀察家》雜誌的編輯,後來在《衛報》有固定的專欄,而且還是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曾經長年住在東德、波蘭和捷克,跟哈維爾與華勒沙變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認為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身邊的顧問,穿梭於學院、政壇和大眾媒體之間,其著作讀者不計其數。老和他筆戰的新左派史學大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帶著貶義地)說他是冷戰末期推倒東歐共產政權最有力的一個聲音。但是直到今天,中文世界才譯出了他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讀者的第一次接觸。雖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可我還是長年閱讀他的著述。且引一句當今左派大紅人齊澤克的話:「儘管他是我的政治對手,我也一直認為他那些豐富的精確觀察仍是值得閱讀的,可以作為東歐滄桑劇變的可靠材料來源。」的確,整個英語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東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是他的本行領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動人的著作《檔案》(The File)當中,他回到德國翻查公開了的斯塔西檔案,發現不少當年圈子中的朋友原來都是祕密警察的線人,曾向當局報告他這個英國人的言行和心理,這個發現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滿陰鬱氣氛的溯往旅程,讓我們看到了人間情誼的脆弱與極權社會最深處的祕密。這種經歷不是每個外國人都會有的;就算有,也不會有他那種專業史學訓練所賦予的識見和涵養,好把這個經歷寫成一部雖然體量不大但是分量十足的深度回憶。
賈頓艾許發現不少當年圈子中的朋友原來都是祕密警察的線人,還曾向當局報告他這個英國人的言行和心理,這個發現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滿陰鬱氣氛的溯往旅程,讓我們看到了人間情誼的脆弱與極權社會最深處的祕密。(取自網路)
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讀者比較熟悉的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作比。布魯瑪的對象是日本和東亞,而賈頓艾許則可說是東歐的布魯瑪。他倆都是記者型的學者,或者反過來說是學者型的記者。從歐威爾開始,記者就已經取代了那種會渲染異國風情和浪漫化自身經驗的傳統外遊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從未去過的曼德勒寫成一首膾炙人口的名篇),成為比較可靠也比傳統學者有趣的外國知識來源。所以當前市面上介紹各國情況的非虛構書籍當中,那些駐外記者的作品總是最受歡迎的。他們曉得怎樣和公眾讀者溝通,又有長年的第一手經驗,有的甚至還具備了相當不錯的學養。賈頓艾許和布魯瑪就是這類人中的佼佼者,是二十世紀後期大眾傳媒國際化年代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有點像人類學家,在祖家和他鄉之間迂迴,因此往往能在一段距離中清醒觀察本地人視而不見的事實,然後再把它們放在另一個框架之中考察省視。當然,賈頓艾許同時還是個歷史學家,他對德國史的了解要比許多德國百姓厚實得多,於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時候就有了一道從往昔深處照下來的微光。
中文讀者比較熟悉的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對象是日本和東亞,而賈頓艾許則可說是東歐的布魯瑪。他倆都是記者型的學者,或者反過來說是學者型的記者。(取自網路)
然而,《事實即顛覆》並非典型的賈頓艾許。因為東歐在他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寫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緬甸,甚至香港。於是問題出現了,他憑什麼去寫那些他沒有長住過的土地?又憑什麼去和當地人溝通(訪談是記者獲得事實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曉當地語言一向是學者型記者的基本要求。賈頓艾許會波蘭文、捷克文與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嗎)?他甚至從來不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他怎能寫那麼多關於歐洲穆斯林的評論呢?當所有通向事實的管道都不是那麼扎實,當事實本身都難以獲致的時候,事實還可能有顛覆的力量嗎?
雖然提摩西.賈頓艾許在牛津大學教書,是個有地位的歷史學家,但他對學院裡的理論發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他不會像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那樣,在史學方法論上細緻探討事實、證明與修辭的關係。他用心的事實問題,是種更接近新聞記者專業關懷,更貼近常識意義,或許因此也更容易為人理解—同時也更容易犯錯—的問題。比如在談到第二次波灣戰爭的時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時任美國國務卿鮑爾的說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當成事實。結果呢?他自然錯了。在整個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像個不好笑的笑話一樣。不只如此,賈頓艾許在那篇文章裡頭竟還說道:「海珊政權是當今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政權之一。他對庫德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還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推翻他對他的國家和該地區而言都是福音。無論戰後的伊拉克會多麼混亂—肯定會混亂,就像戰後的波士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樣—它幾乎已經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實卻顛覆了他當年的判斷,這大概是所有時事評論家的尷尬。
《事實即顛覆》原書出版於二○○九年,賈頓艾許本來有機會刪掉這篇他自己都很後悔當時弄錯了事實的分析;可他沒有。一來,就像他所講的,錯了就是錯了,不掩過乃是道德義務。二來,我猜讓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飾地在那篇文章題目裡頭就已經表達出來的態度;它叫做「為騎牆派辯護」。也就是說,儘管他相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個事實,相信海珊政權垮台之後的伊拉克一定會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輕言美國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反戰派的主張也很有道理,也很說得過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不要忘記,那可是個黑白多麼分明的時刻。布希聲稱:「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中國則有人一邊看著電視裡的世貿大樓倒塌一邊拍手叫好,同時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識分子連署宣布「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戰或不戰,義或不義,幾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而賈頓艾許居然要為騎牆派辯護?沒有立場?那你寫這篇東西幹什麼?他的解釋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熱情洋溢,過分簡單地相信複雜的兩難處境中的一面,即使這樣確實可以讓電視更好看。」他甚至認為,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態度:「我的直覺是,如果你在黑夜中為東尼.布萊爾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將基本上坦承這種自由派的猶豫不決。」「自由派」,就是這裡頭的關鍵詞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像時下中國許多施密特及施特勞斯的信徒所以為的那樣,是批沒有價值傾向的虛無論者。最起碼,自由主義者要相信言論的自由。好比賈頓艾許,他可以同情歐洲穆斯林的處境,但他絕對不能接受因為信仰受到冒犯,於是就理直氣壯地跑去殺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畫家。而且他還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主張「所有神明的信奉者與那些堅持沒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廣場上試一試」;所以他比較不贊成法式啟蒙運動的路子,乾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頭罩還是十字架項鍊—出現在廣場之上。這樣的自由派會擁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權,所以當年他要和哈維爾等東歐異見分子站在一起,主張出版結社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派還會看重一些最顯眼的事實矛盾,不屑於理會對那些矛盾的各種深奧辯解,所以他要說前東德禁止了自己國歌的歌詞(因為它歌頌「統一的德國」),是對自己覆滅的恐懼(因為它害怕會被西德統一)。我們知道,除了前蘇聯和前東德,這世上還真有些政權害怕人民過度認真對待國歌與執政黨的黨歌,而且居然有人辯說那是「複雜國情與時代的錯位,不能簡單判斷」(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賈頓艾許這種自由派看來,你擔心人民把國歌當真,這就是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問題,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煩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付不了種種身分認同困擾背後的激情。在英國人算不算是歐洲人這個大題目上,懂得歐洲並且親近歐洲的賈頓艾許分析過其中各個應該考慮的條件之後,再度擺出了騎牆的態度:「我的結論?沒有結論,這是因為身分研究的本質很少會有明確的發現,也因為英國身分的特質。或許『沒有結論』的聲明本身就是一個結論,甚至還是一個重要又積極的結論。」身分認同也好,政治立場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確的結論,可賈頓艾許這種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卻只能提供傾向。他歡迎前波蘭和前捷克政權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個轉型的困難。所以他當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當成神祇來朝拜的人那樣,不顧現實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憤慨現實的人,走上懷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國家主義的道路。像賈頓艾許這般的自由主義者,總是要在信念支撐的理想傾向與層出不窮且困擾理想的事實之間,進退猶豫。
由於《事實即顛覆》離開了賈頓艾許熟悉的安全地帶,因此他在這部文集裡頭變得更像那些什麼國家的事都能夠暢談一番的「國際問題專家」,這部書於是就更能考驗他身為記者、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能耐了。又由於他在事實材料的擁占上不具優勢,所以帶動他寫作的信念和傾向就會變得更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戰。他是個記者,把自己的寫作類型規定為「當下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誤會,這不是傅柯所說的那種「現在如何成為現在的歷史」,而是冷戰「圍堵理論之父」喬治.凱南推介的學術與新聞的混合寫作),所以他當然要發掘事實,最大程度地親近現場。但他究竟是個歷史學家,就算不愛談太過哲學化的史學方法論,卻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從現場帶回來的材料:
一九八九年,布拉格天鵝絨革命期間,瓦茨拉夫.哈維爾身邊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燈劇院一間奇特的玻璃牆房間裡會面,做重要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是唯一在場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個人拿著一本筆記本,試圖記下他們說的話。我記得當初想:如果我不記下來,就沒有人記下來了。像大多數歷史一樣,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但是這樣寫成的歷史,基礎是多麼脆弱……記憶問題就是見證人問題的核心所在……記憶是一個可以重新加工的CD,會受到不斷地加工,而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僅讓我們理解故事,還讓我們感到更加舒服。
歷史學家賈頓艾許疑慮的,大抵就是這種舒服,把事實裁剪修整得較為合體,較為符應論點邏輯的舒服。老式英國自由派賈頓艾許所疑慮的,則是讓自己皈依某個既定立場的舒服。他寧願讓理想和傾向不停在現實上頭對焦,找不著安穩的落腳之處;他寧願讓現實持續地發出噪音,擾動理想世界的安寧。所以他總在猶豫、進退。在我看來,這樣的態度,或許就是這本書值得當今世人一讀的理由。
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英國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聖安東尼學院以賽亞‧柏林教授研究員,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為《衛報》、《泰晤士報》、《紐約書評》等報刊撰文,並出版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檔案羅蜜歐》、《吾民》以及《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政治寫作》。
*香港知名文化人、傳媒人。本文選自作者為《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政治寫作》(提摩西‧賈頓艾許,印刻文化出版)所作之導讀。
《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政治寫作》,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著,印刻文化出版。(印刻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