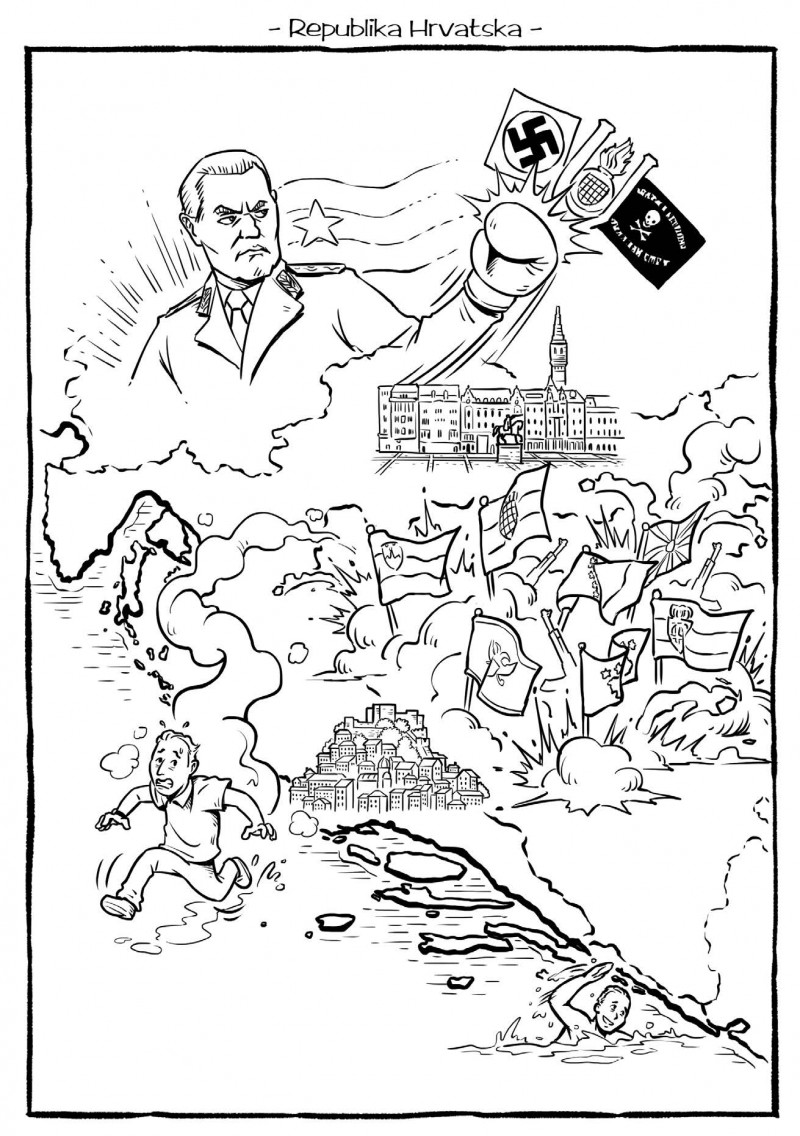克羅埃西亞小資料
位置:巴爾幹半島國家,北邊有斯洛維尼亞跟匈牙利,東邊有塞爾維亞跟波士尼亞。
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台灣的1.6倍)
人口:約400萬(台灣的0.17倍)
首都:札格雷布
主要族群:克羅埃西亞人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17,338美元(2022年資料)
當我首次進入克羅埃西亞時,我從未料到自己有一天會在此地定居超過一年。我放任自己在首都札格雷布(Zagreb)的漂亮街道胡亂打轉,路過幾間高雅的餐廳和店家之後,誤打誤撞來到耶拉契奇總督廣場(Trg Bana Jelačića)附近的多拉茨(Dolac)果菜市場,沒過多久又愛上了聖馬克教堂色彩繽紛的棋盤式屋頂。札格雷布固然是個值得拜訪的城市,然而連最自豪的市民都會承認,克羅埃西亞的王牌景點是令人如癡如醉的達爾馬提亞(Dalmatian)海岸。
往後快轉六年,安娜和我正沿著達爾馬提亞海岸線開車,希望在日落前找個適合紮營的地方。「那邊!右轉!」我指向一條砂石小徑,安娜趕緊踩煞車急轉彎。我們在一個葡萄園旁找到隱蔽的位置停車,在附近設置營地。我們已筋疲力竭,為了盡量利用白天時間觀賞海景,我們凌晨四點就離開斯洛維尼亞,在前往希貝尼克(Šibenik)的途中停頓數次,其中最棒的一個點是帕克萊尼采(Paklenica)國家公園,那是個攀岩者的天堂,亞得里亞海的美景盡收眼底。我們也花了數小時遊覽札達爾(Zadar),一個街道井然有序的威尼斯城鎮。最後我們利用黃昏時刻在希貝尼克逛了一圈後,就開車離開海岸,尋找一個隱密的地方露營。隔日的行程類似,我們打算在日出前離開,以免引起任何人的懷疑,並盡量運用白天,繼續照此模式朝南前往杜布羅尼克(Dubrovnik)。不過,在談到那段故事之前,我們得先做好定位。
你才東歐,你全家都東歐
在討論地理的時候,有些人會把事實與內涵混淆。我們已經見過許多類似例子,東歐人不喜歡被定位於東歐,但這是個極端單純的事實:如果要把歐洲分為東西兩半,其中一半就必須被稱為東歐。他們之所以會反抗,是因為不喜歡「東歐」這個字眼的負面內涵。連一位住在克羅埃西亞的美國人都告訴我:「克羅埃西亞不在東歐,我們在中歐。」是啊,你和所有的東歐國家都是。
(相關報導:
立陶宛─昔日東歐最強大的帝國:《野生的東歐》選摘(1)
|
更多文章
)
人們對「巴爾幹」這個地名也有類似的負面觀感。巴爾幹是歐洲東南部的一個地理區域,它的名字來自位於保加利亞的巴爾幹山脈。根據傳統地理學,歐陸希臘是它的南方邊界,東方和西方分別為黑海和亞得里亞海,多瑙河和薩瓦河則構成巴爾幹的北方邊界。照此分法,斯洛維尼亞不到一半屬於巴爾幹地區,羅馬尼亞只有極少部分,所以把它們排除在外是合理的。然而克羅埃西亞的多數領土都在薩瓦河以南,想當然耳,它理應被歸類於巴爾幹地區,我們只是不能對克羅埃西亞人這麼說。根據二○一○年蓋洛普的巴爾幹監測訪查(Balkan Monitor),當被問及個人是否對巴爾幹地區有認同感時,克羅埃西亞人有百分之七十二回答「只有一點」或「完全沒有」。
這是因為巴爾幹地區就像東歐,會給人不好的印象。在《巴爾幹的隱喻》書中,一位保加利亞作者承認該區域有些「不可否認」的事實:「血腥的戰爭、政治的曖昧與不理性、國家主義的恐懼、毫無意義的分裂與弱化、政府亂象、貧困、經濟與知識的落後。」作者甚至將他的家園形容為「一個被壓抑的歐洲惡魔汙染的王國,充斥著殘酷暴政、大男人主義、民族狂熱、野蠻凶殘、愚昧無知、傲慢自大、毫無拘束的性欲......」喔,他忘了提到他們也有很多美食和美女。
基於如此負面的刻板形象,正如東歐人會抗拒東歐的標籤,克羅埃西亞人也會玩相似的閃避手段。例如首任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Franjo Tuđman)的競選口號就是「圖季曼不代表巴爾幹」,那就像在說「拜登不代表北美洲」。圖季曼從華府歸國後驕傲地說:「美國已保證會全力支持我們,克羅埃西亞絕對是屬於中歐,而非巴爾幹地區。」我很好奇美國是否也曾向巴拿馬保證它不屬於中美洲。我們之後會再辯論此隱喻是否真確,然而地理上的定義是無庸置疑的,因為克羅埃西亞確實多半都屬於巴爾幹地區。
我們可以再釐清一些數據和術語。克羅埃西亞現今有四百萬人,跟一九五○年代的人口相同,也等同於路易斯安納州,面積跟西維吉尼亞州相似,緯度接近奧勒岡州。我們有時會提到「西巴爾幹」,但基本上那包括巴爾幹半島的全部國家,除了保加利亞和希臘以外。雖然有些人會稱克羅埃西亞人為Croat,但我們在此會一律使用Croatian這個字,因為它感覺較順口,而且另一個字聽起來有點像「翹辮子」(croak)。
最後,我們會用「巴爾幹人」(Balkanian)這個新術語定義所有來自巴爾幹地區的人。這是個中立的地理名詞,雖然嚴格說來它可以包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科索沃和馬其頓,但我們在此主要是指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蒙特內哥羅和塞爾維亞,因為這四個國家的人除了住在共同的地理區域之外,他們也有共通的語言。
四個國家,一個語言
一位克羅埃西亞人曾經告訴我,他們在美國找工作時有個常用伎倆。他們會在履歷上寫自己會講四種語言:波士尼亞語、克羅埃西亞語、蒙特內哥羅語和塞爾維亞語,不知情的美國人就會肅然起敬地說:「哇!你是愛因斯坦再世!你被錄用了!」這個美國蠢蛋不知道的是,那就像在說你能精通英語、澳洲語、加拿大語和美語。
(相關報導:
立陶宛─昔日東歐最強大的帝國:《野生的東歐》選摘(1)
|
更多文章
)
語言學界的永恆辯論是:語言和方言究竟有何不同?理論上,語言之間的差異應該比方言大,但實際上兩種斯洛維尼亞方言的差異卻比挪威語和丹麥語之間的出入還多。語言學家無法在標準定義上取得共識,所以我就用常理判定:如果兩人可以在完全理解對方的情況下溝通,他們說的就是同一種語言或方言;如果他們可以理解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九,他們說的就是同一種語言中的兩種方言;如果互相理解的程度不到九成,他們說的就是不同語言。我們可以繼續爭論確切的臨界值該放在多高,或是這個定義該不該包含寫作文字,但這個整體概念可說是直截了當,也合乎邏輯。以此類推,許多不同風格的英語都可歸為同一種語言中的各種方言,而少數特異的斯洛維尼亞方言則可被定義為不同語言。這個系統並不完美,畢竟語言難免有些灰色地帶,但起碼勝過目前那些既不規則、又不合理的方法。
同理,波士尼亞語、克羅埃西亞語、蒙特內哥羅語和塞爾維亞語其實都屬於同種語言的方言,也有人稱之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根據我和數百名巴爾幹人的討論結果,他們也證實自己可以理解對方九成以上的話。當然就像許多語言,他們也有好幾種方言,查方言(Čakavian)在達爾馬提亞海岸很普遍,卡伊方言(Kajkavian)是克羅埃西亞北部的通用語言,舒特方言(Štokavian)則是所有其他地區的主流(它們的名字就是來自當地人說「什麼」的方式─Ča, Kaj, Što)。還有一些子方言的發音差異可以改變一個字的拼法,因為巴爾幹人都是照發音拼字,例如belo(白色)可以寫成bijelo,而mleko(牛奶)也可以變成mliko或mlijeko。有些單字的差異很顯著,以下是一些塞爾維亞文和克羅埃西亞文的對照:šargarepa和mrkva(紅蘿蔔),šlem和kaciga(頭盔),helikopter和zravomlat(直升機,直譯為「空中移動物」)。
話說回來,英語和美語之間也有許多不同,但我們並不會稱之為不同語言。英國有些字的拼法略為不同,有時發音甚至會讓美國人聽不懂;同樣的,一名德州人在倫敦說話可能也會被誤解(光是在芝加哥就可能會)。在英國搭電梯要說lift,不能說elevator;他們的娃娃車是pram,不是stroller;他們穿的褲子是trousers,不是pants;路邊的廣告招牌是hoarding,不是billboard;當他們的卡車沒油,就要幫lorry加petrol,不是幫truck加gas。即使有這麼多文字差異,英國人和美國人仍然都自稱會說「英語」。南斯拉夫語言之間最顯著的差異是在字母系統。塞爾維亞人習慣用西里爾字母,其他人則偏好用拉丁字母。乍看之下,光是這點就足以將它們分類為不同語言,看看Kraljevina Srba, Hrvata i Slovenaca和Краљевина Срба, Хрвата и Словенаца這兩句話,由於字母的長相是如此不同,不懂的人很容易就會把它們視為完全不同的語言。然而它們不但意思完全相同(意思都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與斯洛維尼亞人的王國),連唸法和字數都一樣,因為兩套字母系統都有互相對應的三十個字母,例如拉丁字母c的發音跟西里爾字母ц完全相同。因此如果一名克羅埃西亞人肯花幾個小時背誦三十個西里爾字母,他就能像當地的塞爾維亞人一樣寫出流暢的塞爾維亞文,也能輕易閱讀任何塞爾維亞書籍。另一方面,雖然西里爾是塞爾維亞的傳統文字,但他們也都能讀寫拉丁字母,而且西里爾也逐漸不再那麼普及,全球化的趨勢已經促使多數塞爾維亞人使用拉丁字母。簡言之,兩套字母的外表雖有巨大差異,但那只是假象。
(相關報導:
立陶宛─昔日東歐最強大的帝國:《野生的東歐》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發生在安娜和我不小心開車進入塞爾維亞的時候,每當我看見一個用西里爾字母寫的標誌,就會把它唸出來,因為我會辨認西里爾字母,而她不會。其實我並不懂那些字的意思(我只是照拼音唸),但安娜一聽就會懂,因為她會說克羅埃西亞語,她只是沒花那一絲心力去背誦西里爾字母。說起來也滿諷刺的:一個美國人可以唸出塞爾維亞的文字,卻完全不懂自己在說什麼,而一個斯洛維尼亞人雖看不懂卻聽得懂,因為她會說克羅埃西亞語。
幸運的是,只有被徹底洗腦的國家主義者才會宣稱波士尼亞語、克羅埃西亞語、蒙特內哥羅語和塞爾維亞語之間有任何實質差異,不幸的是,多數巴爾幹地區的知識分子、政客和語言學家都是被徹底洗腦的國家主義者。克羅埃西亞的語言學家是最大的元凶,他們堅持要翻出塵封的書冊,強行將古老文字塞入現代詞彙,試圖抹滅塞爾維亞文化對他們語言的影響。難得世界上有另一個國家能了解他們的冷門語言,他們卻不知心存感激。
克羅埃西亞的語言學家堅持翻出塵封的書冊,強行將古老文字塞入現代詞彙,試圖抹滅塞爾維亞文化對他們語言的影響。(Unsplash)
相似的,塞爾維亞的沙文主義者也想全面推行西里爾字母,廢除拉丁字母;波士尼亞的語文狂想家喜歡大肆宣傳那一丁點的「土耳其色彩」;蒙特內哥羅人則吃飽沒事幹,在字母裡添加ś和ź,刻意凸顯一些微乎其微的差異。這些極端主義者其實都在原地踏步,因為他們對抗的是排山倒海而來的全球化,而現今眾人的目標是尋求共同點,不是製造更多對立。正如某本百科全書所言:「英語和美語之間的拼音變化遠大於那些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系之間的差距。」
最後還有一道難題,要為這四個國家的共同語言想一個好名字。多數語言學家會說它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但這會誤導人,因為它忽略了波士尼亞和蒙特內哥羅。他們應該叫它「南斯拉夫語」,但現在已經太遲。另一個選擇是「南方斯拉夫語」,但贅字太多,而且缺乏創意。有些人用過B C S(波、克、塞三國的縮寫),但那樣就遺漏了最有趣的蒙特內哥羅人;話說回來,B C M S(四國縮寫)會讓人聯想到B D S M(性虐待行為),有些人可能會因此太興奮而無法專心學這個語言。
為了增添一點吸引力,我曾經考慮用Bocromos(BoCroMoS,另一種縮寫法),這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它有兩個缺點。第一,Bocromos聽起來有點像某個被遺忘的希臘方言,不像斯拉夫語。第二,如果哪天巴爾幹地區的政治版圖再度變色(這是遲早的事),這個名字也會隨之過氣。比方說,萬一佛伊弗迪納宣布脫離塞爾維亞而獨立(機率極低),它就可以遊說大家將Bocromos改成Bocromosev(se來自塞爾維亞,v來自佛伊弗迪納)。而如果他們明天全部統一而成為波士尼亞帝國,他們的語言就會變成「波語」(Bo),感覺也很糟。如果用該區域的某樣共同物品來命名呢?他們都吃切巴契契肉腸(ćevapčići),所以何不稱他們的語言為切巴契語(Ćevapčian或Chevapchian)?或是把它取名為布雷克語(Burekian),因為到處都能吃到美味的burek(包滿乳酪、肉泥或菠菜的酥脆薄餅)?可惜這種方式也會衍生問題,特別是那些高傲又毫無幽默感的國家主義者勢必會抗議,就像那些揮舞國旗的美國人也不會希望自己的語言被稱為「漢堡語」、「可樂語」或「麥英勞」。
於是我們只剩一個差強人意的選擇:巴爾幹語(Balkanian)。這個名字不會隨著他們的飲食而變化,無論他們重新統一或分裂成三十七個國家,他們的語言依然可以是巴爾幹語。許多國家都是用同一個字代表其語言和人民,所以巴爾幹語這個字也可以如此通用。因此我們接下來也不會再刻意區分四國語言,它們都是巴爾幹語,只是有四種主要方言,各自還可細分出子方言。如果那些超國家主義者因為這樣就心臟病爆發,他們應該去拜訪拉丁美洲或任何英語國家。那裡沒有人會說阿根廷語、厄瓜多語或尼加拉瓜語,他們講的都是西班牙語;同樣的,沒有人會說澳洲語或加拿大語,他們講的都是英語。我們可否暫時跳脫這種膝腱反射式的民族狂熱?請大家停止揮舞國旗五分鐘,理性思考一下。
(相關報導:
立陶宛─昔日東歐最強大的帝國:《野生的東歐》選摘(1)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