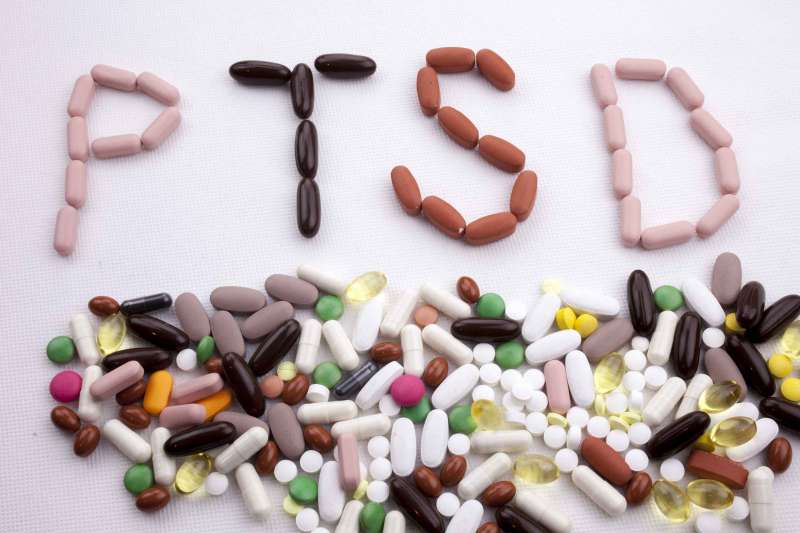家內性侵的心理創傷研究:「為什麼說謊?」「這種爸爸真是禽獸不如!」「你吃這些藥就會好」......這些是家內性侵受害者常聽到的話,卻也是將之推向孤立邊境的話。本文濃縮自不同受害者的生命篇章,中研院民族所的彭仁郁副研究員,透過臨床田野訪談與精神分析,希望幫助理解受害者內心的真實黑洞。
受到本土臨床心理學家──余德慧老師的啟蒙,自臺大心理系畢業後,彭仁郁先在「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接觸到人類學與社會學,後至「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臨床人文學院」,學習更全面地關照受苦之人的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學知識。(圖/張語辰攝,研之有物提供)
家內性侵:讓空氣凝結的話題
「九零年代初期,我在臨床實習時,原以為醫院是安全的環境,可以和心理學專業的同儕、學長姐討論家內性侵的議題,但說出口的當下空氣卻凝結……」彭仁郁回想。無論是大眾或專業工作者,面對「家內性侵」或稱「亂倫暴力」的議題,在毫無準備之下,往往不知如何反應才適當。
彭仁郁提到,我們會想像家內性侵的受害者一定會有某種樣貌,以至於當他們訴說創傷經驗時,我們會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把他們當成脆弱的易碎品來對待。
這樣小心是好的,但過度先入為主去預設樣貌,反而會和家內性侵受害者錯身而過,不見得是他們希望得到的肯認。
時間回溯到高中時期,住在宿舍的彭仁郁和室友熟了之後,幾名同學無意間聊起了被性騷擾的經驗,當大家一個一個分享,才發現「原來這不是只有我在面對」。但對於十多歲的孩子,通常覺得要躲起來處理,因為很多加害者就是自己家裡的長輩、或鄰居。
為什麼家內性侵受害者「不說出口」,這需要從幾個面向來理解:家庭的保護者和加害者常是同一人、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主流臨床精神醫學診斷的限制、與社會對事件妖魔化的壓力。
心理創傷:曾發生的,彷彿沒發生過
曾在醫院急診室、社福機構等單位服務,彭仁郁發現在這些場域和家內性侵受害者接觸時間過短,彼此只能停留在醫病關係,大多互動為開立心理創傷證明、或創傷急性效應舒緩等流程,無法深入了解受害者的生命真實樣貌。
因此,彭仁郁在法國與台灣期間,主動進入家內性侵受害者自組的救助協會,也透過研究計畫與受害者們深入訪談,在臨床人文學、心理學、精神分析的先備知識下,聆聽受害者的生命經驗,並協助梳理受害者難以言說的心理創傷。
家內性侵受害者,常表現這些狀態:發生過的彷彿沒發生過、覺得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圖/iStock,研之有物提供)
與童年受虐或性侵的受害者們訪談時,彭仁郁發現許多受害者不太敢使用「意象」的語言,彷彿一但開始想像,就會召喚真實的受害場景,當時的恐懼會活生生地侵襲感官。大多數人可以明確區分夢與現實,但對於曾受到家內性侵創傷者而言,在幻覺與真實之間,出現了模糊地帶。
有位受害者花了五年的時間,才有辦法說出「我難過」這三個字。因為在這之前,爸爸打他不准哭,一哭打得更厲害。身體明明在痛,又要假裝痛不存在。持續處於撕扯狀態。
精神分析也會用「感官爆炸的後延效應」來解釋這個「症狀」或創傷狀態。當家內性侵受害者受到毆打、性侵、辱罵,心靈的自我防禦機制會在當下阻斷記憶這些片刻,但身體卻會記得這些痛覺,並延宕至未來。成年後,受害者一旦感到精神壓力,這些身體痛覺會立刻回來,因此許多受害者在訪談時回憶起過往,會不自覺伸手阻擋臉部、表情恐懼,甚至觸發歇斯底里的狀態。
長期下來,受害者的「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界線漸漸變得不那麼明確,曾發生過的事件連自己都不敢確定發生過(即「負向幻覺」),然而,一旦試著拼湊腦海的圖像,將它化為語言文字,就會感覺此時此刻正身處充滿痛楚的場景。
正因為受害者無法說清楚這些創傷經驗,進入診間時常被簡化地診斷為重鬱症、恐慌症、思覺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等疾病,並給予藥物消除症狀,例如抗憂鬱劑、抗焦慮劑,卻忽略受苦的核心。
全球的心理治療室裡正在發生:創傷主體被餵食大量精神藥物,心理治療被化約成再適應或再教育的矯正術,創傷主體被鼓勵遠離、或遺忘釀成心理創傷的集體社會文化因素。(Sironi 2007; Bracken and Petty 1998)(圖/iStock,研之有物提供)
然而,國際上已有許多醫學人類學和臨床實務研究指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的標準化診斷,忽視了創傷主體經歷哪些事件、不同人之間的殊異性,往往造成令心理創傷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弔詭。
心理創傷:我,不存在這個世上
另外,家內性侵受害者也經常表示「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在家人眼裡我什麼都不是」。受害者的自我邊界是溶解的,因為加害者不容許這個邊界存在。彭仁郁與許多受害者訪談發現,家內性侵的加害者──長輩、親戚,常常視受害者為自己的「延伸物」。
受害者在生長歷程中,不斷在原生家庭的加害者眼中尋找自我,卻只看見自己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存在。
作為自我認同基礎的「家」,經常由「迫害」──「情感依附」等衝突對立面構成。這樣的狀態從幼童成長至青少年、甚至是進入社會後,難以與他人產生連結,因為「我」本身沒有被賦予存在的權力。
受害者不斷對加害者和依附者的一舉一動察顏觀色,認定自身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服務加害者的需求,以至於不被容許有自我界線、沒有「自我之膚 (ego skin) 」能包圍、涵納自己的情緒,因而也難以命名自身感受。當思想、言行、感受超出被容許的想像界線,會感到錯置的罪惡感,甚至會產生受創的思考邏輯:揭發(告發) = 攻擊加害者 = 家的撕裂和毀滅。
「被性侵為什麼不逃?」、「幹嘛不告加害者!」──通常聽到家內性侵受害者的故事,正義的旁人會提出這樣的質疑。(圖/iStock,研之有物提供)
彭仁郁與受訪的創傷主體試著透過隱喻,間接描繪創傷主體的「心靈地景」所呈現存在內心的恐懼與矛盾。
比如,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和反應,讓彭仁郁聯想到一個畫面,她把自己內心的畫面跟受訪者分享:「你好像是一隻受傷無助的小動物,生在一個有兇狠野獸的山谷裡。野獸告訴你,牠們是你的父母親,但是動不動就咬你、攻擊你,還要求你被攻擊了不准哭、不准叫、更不准逃走。這個可怕的山谷不是你想像中期待的家,但是你好像沒有辦法離開,為什麼?」
聽到這樣的畫面,受訪者沉默許久後,說道:「因為我對這個山谷的每個角落都很熟悉,雖然有野獸,我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會在哪裡出現;也知道牠們憤怒的時候,只要把自己丟給牠們吃,牠們滿足了就會安靜下來。如果離開這裡,就算理智上我知道可能別的地方野獸比較少,但是我怎麼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沒辦法預測,這是更可怕的!而且,我怎麼知道表面上看起來像人的人,會不會在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變成野獸?」
(相關報導:
性犯罪受害者不再沉默》一個「靈魂最深最黑暗」的故事 開啟社群網路「我也是」浪潮
|
更多文章
)
彭仁郁提醒,如果旁人沒有意識到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只要讓受害者感受到一丁點不信任感,就可能會逼迫受害者「說謊」,亦即「我先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但我同時加上其他沒發生的細節,或移動事情發生的時間順序,好混淆視聽。因為當我察覺到你可以定位我的時候,我就感到不安全」。許多社福機構或檢調單位,在尚未建立信任感、沒有意識到這個心理狀態下,可能會因而對家內性侵受害者前後不一的說詞感到納悶、產生誤解。
當受害者無法言說創傷,請借用你的感受
創傷憶痕的幽微糾結,使得有意識的噤聲、或無意識的失憶,成為家內性侵受害者重要的倖存策略。要如何在訴說與聆聽之間建立信賴,並深入了解受害經歷?
透過臨床田野一次次與不同的家內性侵受害者訪談,彭仁郁深深感受到「心靈地景」這個溝通方式的重要。
大部分的受害者到了面前,從外表看不到創傷,但我們不知道他內在淌著血。他要怎麼帶你進入內在世界?只能用想像的語彙、用圖像化的隱喻。
由於家內性侵受害者說不清楚傷痛、害怕說出口的噩夢成真,在訴說與聆聽之間需要建構一個「過渡空間」,讓創傷主體的想像和表達能在這個「過渡空間」安全馳騁,才可能漸漸修復自我內在,減少疲憊地自我放逐狀態。
「你沒辦法感受、沒辦法想像,那就讓我成為你的『容器』,將我的心靈潛意識暫時借給你用。你告訴我感覺,我把我聽到的感覺回饋給你,想像我在你經歷的狀態下可能會感覺到什麼。」彭仁郁說明讓受害者心靈地景浮現的方式,但這只是朝向創傷療癒可能的第一步,而不是終點。
聆聽,是持續通往受害者心靈地景的必要途徑。受過臨床訓練的心理人類學家 Katherine P. Ewing (1997) 曾強調「忍受沉默」的重要。不斷發問、無法容忍對話間的空隙,會顯現聆聽者的焦慮,也透露著對於蒐集某種特定答案的預設框架。
「當你過度相信你已經知道的,都會阻擋你理解活生生的經歷」,彭仁郁很認真地接著說道,「我不會說我是家內性侵心理創傷的專家,沒有任何人可能是。我只是跟很多受害者一起工作、傾聽他們的見證,漸漸能夠理解內心的複雜程度,和潛藏在的核心創傷。」
外界的獵奇與正義,也是受害者的痛源
心理創傷的形成,不只取決於家內性侵的暴力程度,更取決於受害者在這些殘酷生命背景中,如何想像自己存在的樣貌、如何與社會他人連結。因此,心理創傷療癒不應只是給予藥物、消除症狀,而是協助讓受害者能成為一個主體,感覺到自己存在這個世上,並找到修補人際關係網絡的接點。
對於創傷主體而言,每次與他人接觸,都會經歷一次確認自身存在樣態的試煉:「對方看見的是什麼樣的我?」、「對方會接納這樣的我嗎?」
若創傷主體能明確知道自己被安放在他人心中一個位置,令這個值得他人凝視、眷顧的「我」是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修復自我放逐狀態」與「修補斷裂的社會連結」是同步的。
然而,真實情況並不是這麼容易。媒體常用獵奇的「狼父、禽獸」標題來妖魔化家內性侵事件,但媒體正義中的狼父,正是受害者從小依存的爸爸。「我的爸爸在一天 24 小時之內,他可能照顧了我 23 小時,卻也加害我 1 小時。你們罵我的爸爸是禽獸,但我卻是他的小孩,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要怎麼告訴你曾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彭仁郁以受害者的視角點出,情境永遠是複雜的。
一句話在受害者聽來,可以鼓勵他、或使之更消沉,取決於受害者的心理狀態、與發話者和受害者的關係。儘管與許多家內性侵受害者長期工作,彭仁郁仍認為,沒有任何安慰的話語或標準流程,是可以預先準備好,因為每位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另外,許多剛踏入這個領域的臨床工作者,會背負著過大的自我壓力,認為要完全承擔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但這就像有人溺水了,你卻也一起溺水,幫不了任何人」彭仁郁比喻。
我給自己的提醒是;我一隻腳在創傷情境裡,為了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但一隻腳站在外面,為了穩住我們兩個人,不會一起被創傷淹沒。
依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04 年統計資料,家內性侵受害者以 12~18 歲最多 (佔 36%) ,6~11歲次之 (佔 26%)。考量可能有許多通報黑數,彭仁郁參考國外調查與臺灣《蒲公英飛揚計畫》的數據推估:「若國高中或大學班級,班上有 30 人的話,可能約有 2~3 人曾經歷過家內性騷擾或性侵,受害者男女都會有。」這些數據的重要性是,讓受害者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被孤立的,而能透過適當的協助面對心理創傷。
「因為我們都假設家內性侵只會發生在別人家,自己家永遠不會發生。」這句話彷彿一面被拳頭揮破的鏡子,照映著家內性侵受害者求援碰壁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