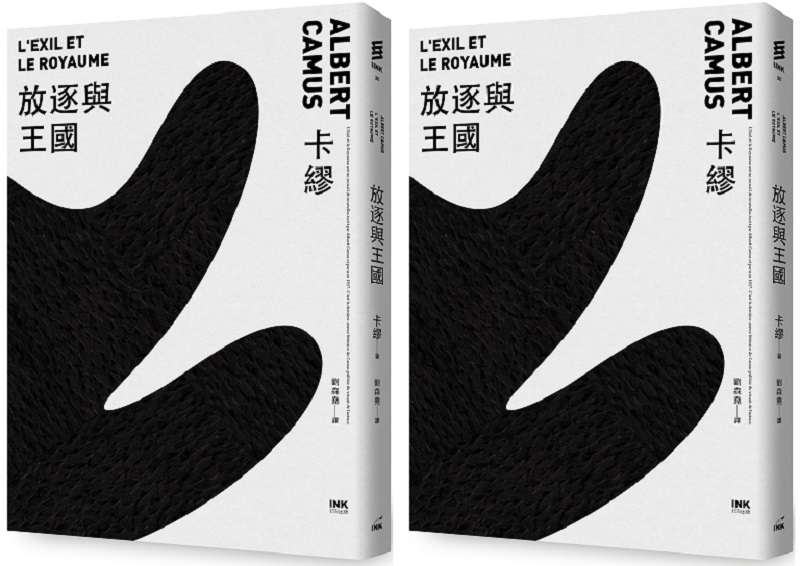小學教師看著那兩個人正要爬上山坡朝他這邊走過來,一個騎馬,另一個走路。他們還沒爬上通往學校路上那處陡峭的斜坡,學校就座落在這個丘陵半山腰上面。他們在雪地裡蹣跚前進,走在一大片荒涼高地裡的石頭中間,走得很慢。每隔一會兒,這隻馬就會晃著頭噴一下鼻,雖然聽不到噴鼻的聲音,卻可以從鼻子噴出來的白色蒸氣看出來牠是在噴鼻。這兩人之中至少有一人對這個地區應該很熟悉,他們沿著一條幾天來已被白雪覆蓋的小徑前進,小學教師估計在半個小時之內他們到不了山丘上。天氣很冷,他回學校裡找出一件毛衣披上。
他穿過一間空蕩冰凍的教室,已經三天了,黑板上以不同的粉筆顏色畫著法國四條河流流向河口出海,還沒擦掉。連續八個月的乾旱之後,在十月中突然下起一場大雪,一滴雨都沒下,天氣就在一夕之間轉壞,散布在平原高地上村莊的二十個學生就再也不來上課了,必須等天氣放晴。達呂只有一個房間,就在教室隔壁,面向東邊的高原地帶,他只需在這個房間生火就行了,房間有一扇窗子,和教室的窗子一樣,面向大南方。 離學校座落的地點幾公里遠的地方,高原地從那裡往南沿伸下去。天氣晴朗的時候,可以看到遠方一大片紫色山巒,越過那裡就是沙漠了。
房間暖和了一些之後,達呂回到窗口,他剛才就是在那裡看到那兩個人,現在看不見了,他們此刻正在爬那陡峭的山坡。天空已經沒那麼陰沉,昨晚夜裡雪停了,早上在模糊的亮光中揭開,隨著雲層的移動,模糊的亮光並未跟著清晰明朗起來。下午兩點鐘,大家會說,一天才要真正開始,但是這怎麼樣也總比過去三天昏天暗地下雪下個不停要好上許多,有時還夾帶著狂風吹動教室的雙重大門。達呂只能耐心待在房間裡,只有偶爾去旁邊小屋照料一下小雞,或是去拿取備用的炭火時,才出去一下。值得慶幸的是,在北邊離這裡最近的小村莊達吉德的小卡車,早在暴風雪來襲的前兩天已經把儲糧送來,他們在四十八小時之內還會再回來一次。
其實,達呂並不擔心暴風雪把他封住,小房間裡堆滿了一袋一袋的小麥,那是政府當局儲放在他那裡的口糧,以便分發給這次旱災受到危害的學生家庭,事實上這些都是貧窮家庭,這次旱災受害最烈,達呂必須每天分發口糧給小朋友們,他很清楚,在這些難捱的日子裡,他們非常需要這份口糧,也許今晚就會有學生的父親或兄長來領取口糧,他們必須忍耐到下一次收穫期的到來。還好從法國運來小麥的船隻現在已經抵達,最艱困的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這場災難很難忘卻,成千上萬的衣衫襤褸的像鬼魂一般的人們在大太陽底下遊蕩,高原日復一日被燒烤著,整塊地都被烤焦了,幾乎焦成像炭了,每塊石頭只要輕輕一踏,立即化成粉末。羊群成千上萬死掉,甚至到處都有一些人死去,只是不太有人知道而已。
(相關報導:
「支持台美企業半導體合作!」酈英傑:透過EPPD建立新經濟關係
|
更多文章
)
在這場災難面前,他在這被遺棄的學校裡生活得像僧侶一般,儘管他能夠賴以為生的東西那麼稀少,他還是很高興,雖然過的是那麼粗糙的生活,牆壁那麼破敗,沙發那麼狹窄鄙陋,他的白色木板書架、他的井水,還有他每個禮拜賴以維生的水和糧食,沒有一樣是富足的,他還是感覺像大老爺那麼高興滿足。然後沒預警就突然下起這場大雪,連事先下場雨來緩衝一下都沒有。這地區就是這樣,生活很嚴酷,沒有人能夠倖免,他在這裡土生土長,要是離開這裡到別的地方去,他會覺得像被放逐一般。
他走出門外,爬上學校前面的土台,那兩個人現在才爬到山坡的一半,他認識騎馬那個人,他已經認識很久的一位老警官,叫做巴杜西,他用繩子拉著一個阿拉伯人,兩手捆綁一起,頭低低的,跟在他後面走著。警官向達呂揮手致意,達呂沒有回應,他正忙著打量後面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藍色帶風帽長袍,腳上穿一雙涼鞋和米灰色棉襪,頭上纏著一條既窄又小的伊斯蘭頭巾。巴杜西緊緊拉著馬,以免碰傷阿拉伯人,他們慢慢靠近,走得非常慢。
等更靠近的時候,巴杜西喊叫道:「從艾勒阿穆爾到這裡才三公里遠,卻走了整整一個鐘頭!」達呂沒有回應,他緊緊裹著那件厚重的羊毛衣,看著他們走上來,等他們來到土台時,達呂說道:「您好,進來暖和一下吧。」巴杜西很吃力地從馬上跨下來,繩子還一直握在手裡,他向小學教師露出微笑,嘴上的小鬍子都冷得豎起來了,他的兩隻眼睛顯得黯淡無光,深陷在曬黑的額頭底下,他的嘴角布滿皺紋,讓他看起來一副很專注的樣子。達呂接過韁繩,把馬牽進旁邊的小屋裡,等到他回來時,他們已經進到學校裡來了,正在等他過來,他把他們引進自己的房間。「等我把教室暖和一下,」達呂說道,「我們在那裡比較自在一些。」他回來房間時,巴杜西已經坐在沙發上面,他早已解掉牽著阿拉伯人那條繩索,阿拉伯人蹲在火爐旁邊,手上的繩子還一直綁著,頭上的頭巾往後拉下,他一直望著窗口。達呂起先沒有注意到他的嘴唇很大很厚,甚至很肥碩,很像黑人的嘴唇,相對鼻子卻很狹窄,眼睛很小,像燒著一股火氣,頭巾蓋著那看起來像是很固執的額頭,由於寒冷,那深褐色的皮膚失去了光澤,整個臉龐看起很憂慮卻又桀敖不馴的樣子,特別是當他轉頭看著達呂,注視著他的眼睛的時候,達呂著實嚇了一大跳。「你們先過去那邊,」小學教師說道:「我來給你們煮薄荷茶。」「謝謝,什麼苦差事!退休萬歲!」巴杜西說著,然後用阿拉伯語對他的犯人說:「過來,你。」阿拉伯人起身走到他面前,舉起綁在一起的手腕給他看一下,然後一起走入教室。
達呂端著茶,另外又拿著一張椅子進到教室,巴杜西早已端坐在第一張學生桌子上,阿拉伯人蹲著靠在講台旁邊,面對擺在講桌和窗戶之間的火爐,達呂要遞茶給他時,看著他仍被縛著的手腕,猶豫了一下。「也許可以把他的手解開了。」「那當然,」巴杜西說道:「那是只有在路上押解時才綁著。」巴杜西噘了一下嘴,然後起身,達呂把茶放到地上,雙膝跪在阿拉伯人旁邊,阿拉伯人半聲不吭,看著他為自己解索,眼睛發著熱光。繩索解開後,他兩手互相搓著已經發腫的手腕,然後拿起茶杯,小口小口喝著滾燙的熱茶。
巴杜西從茶裡頭抓出他的鬍碴,說道:「這裡,孩子。」
「不,我要回去艾勒阿穆爾,你,你押解這位朋友去坦奎特,他們會在鎮上公共社區等他。」
「耶,這是什麼意思? 在戰時,大家什麼職務都幹的。」
「好,但命令就在那裡,而且和你有關,這就夠了。大家都在談下一個暴動,
簡單講,我們在動員了。」達呂擺出一副不肯妥協的樣子。
「聽著,孩子,」巴杜西說道,「我很喜歡你,你必須了解,我們在艾勒阿穆爾這個小行政區那邊只有十二個人在做巡邏工作,所以我一定要回去,他們要我把這個怪傢伙交付給你,不得有誤,然後趕著回去,我們沒辦法在那邊繼續拘留他,他的村子已經開始在鬧事了,他們要求釋放他,你要在明天大白天當中把他帶去坦奎特,二十公里的路程,對像你這麼強壯結實的人是難不倒的,之後就什麼都結束了,你回到你學生這裡,繼續過你的美好生活。」
在牆壁後面,在小屋裡可以聽到那匹馬的噴鼻聲,還有馬蹄在踏地的聲音。達呂望著窗口,天氣已經放晴了,太陽光在積雪的高原上灑射著,當雪全都融化之後,太陽會再度盤據大地,再一次肆虐遍地的石頭,不要幾天的時間,太陽會再度一成不變把那乾燥的酷烈光線照射在這孤絕的大地上,居民早已習以為常了。
「不,一個字都不會,我們搜捕了一個月,他們把他藏了起來,他殺了他表
「我不認為,但我不太確定,我們永遠無法確定這種事情。」
「我想是為了一些家庭的雜務,好像是有一方欠另一方稻穀,我並不是很清
楚,簡單講,他用砍柴刀宰了他表哥,你知道,好像在殺一頭綿羊,喀嚓……」巴杜西作勢把一把刀跨在脖子上的樣子,阿拉伯人被他的動作吸引住,轉頭用很焦慮的眼光看著他,達呂突然對這個阿拉伯人很覺憤怒,他很反對這類基於仇恨的冷血惡劣行徑,他很討厭這種人。
這時火爐上面的水壺發出了叫聲,他又倒了一杯給巴杜西,然後猶豫了一下,也倒了一杯給阿拉伯人,和先前一樣,他很快一口飲盡,他的雙手抬高,把身上的伊斯蘭長袍也拉開了些,露出了瘦而結實的胸膛。
「他們如果來作亂,你就完蛋了,孩子,沒有人能置之度外,我們現在在同一條船上啊。」
「我知道怎麼自我防衛,他們如果來了,我會有足夠時間反應。」
巴杜西笑了笑,然後嘴巴又合起來,小鬍子又蓋住了他那口雪白的牙齒。
「你會有時間反應 ? 你的腦筋總是有點失常,因為這樣,我才那麼喜歡你,我的兒子也是這樣。」
「拿著,我從這裡回去艾勒阿穆爾,身上不需要帶著兩把槍。」
這把手槍放在漆著黑色的桌面上,閃閃發亮,當老警官轉過身來的時候,小學教師可以聞到他身上皮革和馬的味道。
「聽好,巴杜西,」達呂突然說道,「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感到不痛快,首先是你那小夥子,我不會押送他,要我去打仗可以,是的,如果必要的話,這檔事可不行。」
「你在幹蠢事,」他慢慢地說道,「我也不喜歡幹這種事情,我不喜歡,多少年來老是用繩子綁人,我從來沒有習慣過,是的,甚至為此感到可恥,但我們不能放任什麼事情都不管。」
「是的,把我對你說的話跟他們重複一遍:我不會解送他。」巴杜西顯然努力在思考這件事情,他又再一次仔細看著阿拉伯人和達呂兩個人,他最後終於下了決心。
「不,我什麼都不會對他們說,如果你現在要丟棄我們不管,我也不會告發你,我接到命令把這個犯人解送到這裡:現在我的任務完成了。你現在要在這文件上面簽個名。」
「不要為難我,我知道你到時候會說真話,你在本地出生,是條漢子,不過你還是得簽個名,這是例行公事。」
達呂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四方形的小瓶子紫色墨水,一支紅色木製筆桿的鋼筆,底下鑲著上士牌筆尖,這是他向來用來寫帖子的筆,他現在用這支筆簽了名,警官把這張簽了名的文件小心翼翼摺疊起來,放到皮夾裡面,然後走向門口。
「不,」巴杜西說道,「不必那麼多禮,你剛剛冒犯到我了。」
他看了一下阿拉伯人,在原來地方,一動不動,看起來一副很憂悶無聊的樣子,他走向門口。「再見了,孩子。」他說道。門在他背後關上,他出現在窗口,然後又消失,因為地上有雪的關係,他的步伐有點蹣跚不穩,那匹馬在隔板後面躁動著,引起那些小雞驚惶不安,隔一會兒,巴杜西牽著馬又出現在窗口,手上握著韁繩,頭回也不回直接走向前面的土台,他先消失,然後馬跟在後面也一起消失了。這時傳來一顆巨石在緩緩滾動的聲音,達呂回到囚犯那裡,發現他一動不動,看到他來了就一直不停瞪著他看。「等一下,」小學教師用阿拉伯語說道,說著就走向他的房間,走到門檻時,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又折回來,來到桌子前,拿起桌上的手槍放入口袋裡,然後又走向門口,進入他的房間。
他在沙發上躺了很久,四肢伸展開來,望著外面的天空漸漸黯淡下來,聽著四周圍的寂靜無聲。戰後不久時,他初來這裡的前面幾天,最令他感到痛苦的,就是這種寂靜無聲。他當初要求在一些要塞底下的小城一個教書職位,這些要塞隔開高地和沙漠,那裡有許多石頭築成的圍牆,靠北邊的是綠色和黑色,靠南邊的則是玫瑰色或淡紫色,劃分著永恆夏季的邊界。結果他們給他安排的是一個更北邊,甚至是在高地的職位。一開始時,這塊到處是石頭的不毛之地,的確令人感到非常不愉快,特別是孤單和靜默令人更覺難過。有時候,他會看到一些犁溝,以為是人們用來耕作莊稼,結果不是,他們挖出犁溝是為了培養某種特殊石頭,用在蓋房子上面。他們在這裡的一切努力就是為了培養並挖掘寶石,有時他們會蒐集一些土屑,藏在犁溝的窪洞裡,日後用來當作村莊中菜園裡施肥的材料。這個地區有四分之三面積的土地底下藏有寶石,許多城市在這裡誕生、興旺,然後又消失,許多人聚集到這裡來,互愛又互相廝殺,然後死去。在這沙漠裡,不管是誰,包括他和他的客人,都不算什麼,然而,達呂心裡很清楚,他們卻又離不開這裡,只要一離開這裡,就沒辦法真正活下去了。
(相關報導:
「支持台美企業半導體合作!」酈英傑:透過EPPD建立新經濟關係
|
更多文章
)
*作者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作者生前最後一部作品,短篇小說集《放逐與王國》(劉森堯譯,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