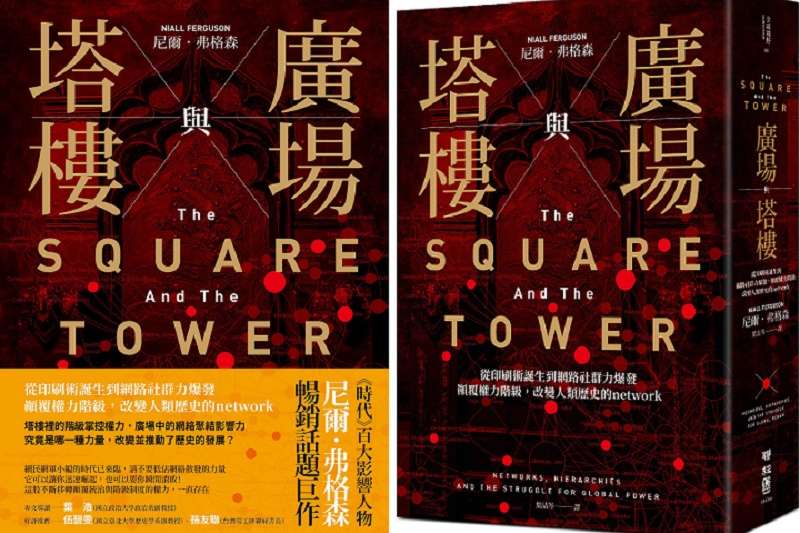用一個方程式來證明,時間是有起點的,是不是很棒,教授?以一個簡單優美的方程式來解釋萬物。
──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
幾年前看過霍金傳記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人,或許記得這位提出宇宙模型來解釋時間起源的偉大物理學家,從學生時代起就想要找一個可以解釋宇宙萬物的理論。或許,一個傑出科學家與天才科學家的差異,就在於後者擁有這種尋找一把鑰匙打開宇宙祕密的瘋狂想法——雖然那一句關於「萬物論」的口頭禪,實際上是語出霍金擔任劍橋大學數學系教授時的一場公開演講,而且說的是這種能統一所有理論的方程式乃自然科學的聖杯,人人想找。

相較於自然科學,人文學科似乎不以尋求這種聖杯為研究目的,因為前者以大自然界為研究對象,關切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以及運作於現象背後的自然定律,但後者的對象卻是具有心思意念和意圖動機的人類自己,且研究的目的旨在理解人類所建構的社會或創造的文化,及其背後的思想理念和事件所表達的意義。也因此,除了某些特別標榜自己是「社會科學家」的史學工作者,會致力於尋找那種可以解釋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或類似事件背後的普遍性模型之外,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會把焦點放在特定事件的細節以及人物身上,意圖讓人們看到每個事件、不同時代以及特定歷史人物的獨特之處。
然而,本書作者弗格森卻不這麼想。這位畢業於牛津,任教過母校以及劍橋、哈佛、史丹佛等名校的英國史學家,似乎有霍金身上那一種狂放與反傳統,且天分也到位。《廣場與塔樓》一書不僅想告訴讀者水平連結的「網絡」(networks)結構之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性,遠高於垂直關係的「階層」(hierarchies)結構,而且史學家自古以來全都搞錯方向、走錯了路,只想透過「大人物」或官方檔案來理解一個時代,而此舉—─借用一下政治評論員納伊姆(Moisés Naím)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評論這本書時用的比喻——猶如喝醉酒的人會在路燈下找鑰匙,而不是在暗處,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看得到東西的地方。
換言之,歷史不該是帝王史或偉人史,那假定了人物的重要性可做出等級區分,依序從大人物到小人物,然後聚焦於大人物身上。史料的採用也不該過度仰賴國家文獻,因為那本身也鑲嵌於一種階層制想像。
唯有網絡才是答案。唯有從人際網絡的角度來建構一幅人物互動與權力交織的圖像,才符合真相,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真正動力!不論是宗教改革的成功與啟蒙運動的興起仰賴了網絡,或大清帝國的「塔樓」階層統治模式和太平天國始於「廣場」般連結邊緣團體的網絡之間的較量,二十世紀蘇聯垮台與冷戰結束的緣由,甚至川普為何能當選美國總統,弗格森幾乎把半部人類世界史以「網絡/階層」概念及其對立模式,重講一次。 (相關報導: 底層青年成為「網絡革命黨」主體:《中國:潰而不崩》選摘(3) | 更多文章 )

弗格森對傳統歷史書寫方式的批評,當然也沒忘記自己。而根據他的坦誠,他本人是在撰寫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授權傳記時,才真正體會到了網絡的重要性,而此前即使包括在一九九八和二○○一年替他贏得不少讚譽,分別關於歐洲銀行家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以及討論從工業時代到網路時代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金錢與權力》(The Cash Nexus)兩本書,也都忽略了網絡所真正扮演的關鍵角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相當鬆散的家族關係或關聯性的理解。當然,前述兩本書足以讓弗格森從牛津大學歷史系這座學術象牙塔,轉到紐約大學的商學院去任教,兩年後再讓哈佛大學商學院挖角,從此逐步建立起自己在美國的人際網絡。然而,是季辛吉本人以長袖善舞的能力建構了一個結合政客、商人、外國大使、國家元首、新聞從業員等在內的龐大人際社會網絡,不能以追求單一目標的階層結構來描繪,才讓作者意識到過去以族譜與姻親關係為核心的關係圖,仍然是一種圍繞於特定甚至單一大人物之上的史觀,既不能掌握季辛吉的權力組成結構和影響力範圍,也不足以應付我們正處的第二個「網絡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