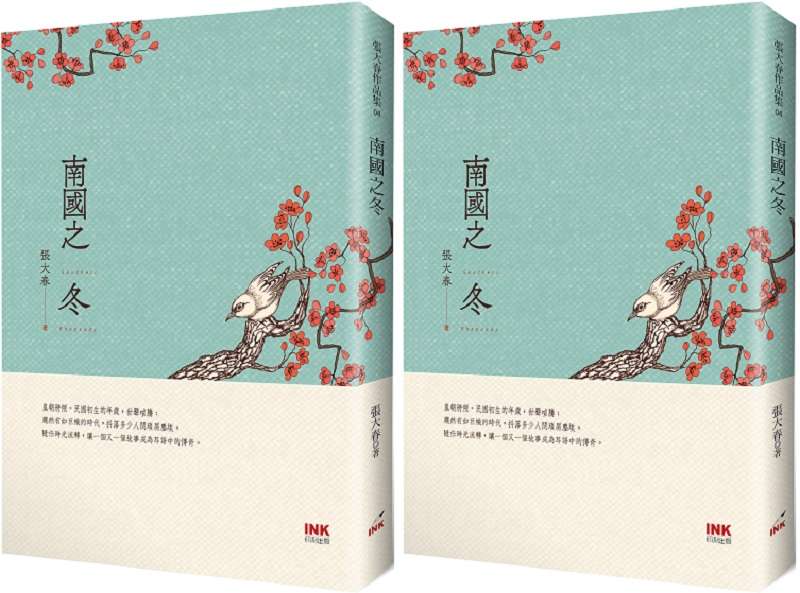「藏王」是有來歷的。傳說杭城裡有河的時代就有這故事了。杭州耆宿都知道:「有河就有幫,有幫就有王。」意思就是說凡事要有「單一窗口」,絕不容令出多門。這裡所謂的「有幫就有王」,就是指「人間藏王」。
杭城原有4條城河。自西而東,分別是浣紗河、施腰河、鹽橋河與菜市河。施腰河又名小河,在城區中間,東起鹽橋河新宮橋之北側,北至洗馬橋接浣紗河出武林門,全長十里,是杭州古河道。聽說這河道在抗戰期間就淤塞了,淤塞的原因是居民長年以來不斷傾倒糞便垃圾之故。民國35年索性修築成馬路,叫光復路,這路才修成就往下陷,所以當地人常拿「光復」、「陷落」兩個詞開玩笑,大意不外:「怎麼才光復又陷落了?」1949年政權更迭,關於這條「糞底兒路」的流言俗諺,可謂一語成讖。
杭城市裡走船,例有專職船夫。四河船夫分兩幫,浣紗、施腰二河一幫,叫「清湖幫」,因為浣紗河舊時又名清湖河之故;鹽橋、菜市二河是另一幫,叫「運河幫」,因為菜市河舊時又名運河之故。這兩幫各有幫主,平時互不往來,只在一年三節以及祭河伯的日子,兩幫會合力主持典禮,迎賓酬神,揖讓升飲,俱能中節有度,稱得上是相當平和的地方勢力團體。
這兩個幫,有一名義上的共主,叫「藏王」。「藏王」是一脈單傳,誰也不知道他會將這共主寶座傳給誰,且多少年下來,十之七、八,是不傳給這兩幫弟子、而盡付於外人的。最有意思的也在這裡:共主的寶座──在幫中人丁看起來──是誰也不想坐的。
這又怎麼說呢?打個世俗的比喻吧,杭河二幫行的是「虛位元首制」,兩幫原本非親亦非故、無怨亦無仇,各做各的生意,賣的都是勞力,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利市,是以即便當上共主,既發不了財,也改不了運,孬好還就是個撐船的。可一旦當上了「藏王」,撐船的時間就少了。因為每一位「藏王」都有個使命,非得在任上完成不可;那就是物色下一任的「藏王」,物色到了適當的人選還不算完差,還得傳授一門「藏王功」。少則10年,多則20、30年,把前任所傳下來的這一門技藝完完全全再傳授給新任,才算是交卸了職責。所以「藏王」的閒事不少,卻肯定賺不了什麼錢,身上只有一樣值點兒銀子的東西:一個銅缽兒,可以到處要飯吃。據說在前清時代,上杭州常見的「門板飯」飯鋪嗑一頓,憑著手上的缽兒,只一個制錢就許吃一頓,還外帶一勺子又香又濃的「澆裹」。
你還可能會問:不是有一門「藏王功」嗎?世論言及功法,不是強身,就是會武,養生自衛帶嚇人,也算是了不起的能為了。然而,事實擺在所有人的眼前,從古至今,沒有外人知道過:那「藏王功」是什麼玩意兒?究竟練得成、練不成?什麼人才、花什麼力氣才練得成?練成了又有什麼得利得便之處?沒有人知道。至少,除了「藏王」之外,沒有人知道。
杭城河幫起源甚古,甚至早於庵清、早於糧米幫,還有說宋代就有「清湖」、「運河」兩幫了。「清湖幫」和「運河幫」原本各自勞力營生,之間既無瓜葛,也無芥蒂。不過,施腰河在城區中間,東起鹽橋河新宮橋之北側,北至洗馬橋接浣紗河出武林門,全長十里,是杭州古河道,為兩幫交接之地。人說船過水無痕,水世界茫茫蕩蕩,也並沒有地標;你幫之船、我幫之船,就算划過了界,冒出去三、五里地,也不該有什麼計較的。
偏偏在新宮橋和洗馬橋之間,船夫與船夫常有些摩擦。人就是這樣,有計較處且計較,沒計較時找計較。有那麼一回,為了這沿河十里的迎送往,兩幫鬧起意氣來。運河幫裡一個船夫拿篙子打破了清湖幫裡一個船夫的腦袋,攪得浣紗、施腰二河裡3天找不著駕船的──這兩河的人丁連夜把手下所有的船隻拉上旱路,一總堵上了鹽橋、菜市二河的各個渡口;這就是要打混仗了。
有人報了官,縣父母其實早就得著清湖幫方面的稟報,揚言官府裡不得干預,否則本幫之人拚死也要殺盡另幫之人,那麼一來,杭州城裡的水路交通就非癱瘓不可。
可是官裡不管,兩幫打得就更野了!從船上打到水裡,再由水裡打到橋上,足足打了2天2夜,打著打著肚子餓了,招呼一聲便各自收手,找一爿門板飯鋪嗑上一大碗「門板飯」,吃飽了再回原地打去。
有那麼個清湖幫裡的愣小子,長得高頭大馬,平日手上使的篙子也特別長,就在混戰之中,這愣小子一篙杵對方不著,重心盡失,連人帶篙有如今日那撐竿跳的選手一般,筆直倒栽入水,說也奇怪,一栽下河,就沒了頂,別說人沒上來,連篙子也不見了。
這是極不尋常的事:一根竹篙子,怎麼會浮不起來呢?這是開打之後的第2天黃昏,眾人又廝纏了大半夜,終於有個運河幫裡的癩痢頭船夫覺得過意不去了,打著打著,把手上的傢伙一扔,道:「不成!那大塊頭死活得有個交代!」說著便跑回現地,一頭跳進水裡,隨即也滅了頂。大個子、癩痢頭分屬兩幫,各有各的朋友,當然都不免心焦,可自凡是誰在那塊水域裡下去尋,就算是尋著了什麼也不會有別人知道──因為無論是誰,一旦下去了就上不來了。直到天大亮,兩幫裡連先前那兩口子算上,一共滅了7頂。
就在這時,武林門外踅過來一個身著一襲嶄白絲袍,劍眉星目、器宇舒朗的後生,見眾船夫圍觀議論,便笑著說:「這是驚動了河龍了!」
眾船夫聞言,不由得面面相覷,一時紛紜議論起來,有那年長些的,很聽不得年輕人大放厥辭,遂斥道:「老夫在這河裡撐了50年的船,從沒聽說過有什麼河龍的。」
「在山是山龍,在河是河龍,山山有龍,河河亦有龍;龍在山則興雲布雨,在河則鼓風作浪,有什麼稀奇?」那白袍少年說:「這浣紗、施腰、鹽橋、菜市四河原就是一龍之四爪,此龍潛修千年,正要化行於天,卻叫你們這兩幫混混攪擾,千年修行,眼見就要毀於一旦了,人家,能不忿忿麼?」
(相關報導:
在試用期離職,就要賠償高額違約金是合法的嗎?律師為你一次解答
|
更多文章
)
才說著呢,這河道之水就像是條被人給抖擻了一下的布匹,打從遠處滾著不高不低整整三尺的排浪湧了過來。此時無風,如何能夠起浪?這且不疑它,浪頭由下游翻滾回上游,更是千古奇觀了,看得眾人膽一戰、心一驚,悉數朝河面跪了下去。
那白袍少年又道:「諸君且將你們的船都繫了,待我同那河龍說上幾句。」
目睹此景,又聞聽此言,船夫們哪裡還敢叫囂頑鬧,紛紛下河去繫船,也有船和船夫不在現地的,自有人前去招呼知會,這就不煩贅述了。且說這白袍少年打從袖筒裡取出一個金光閃閃的缽兒來,念了聲:「阿彌陀佛!」隨即將缽兒高舉過頂,眼睛則垂視著河面,喃喃說道:「我聽說龍出則水湧山崩、風馳電掣,經常損毀禾麥田廬,今番若非我道經此地,汝這孽畜恐怕還是要傷及無辜的。我既然已經來了,汝何不先發還那幾條性命來,我也好記汝一筆功德。」
話才說完,那河面近橋之處猛可噴起一根徑寬尺許的水柱,一柱噴出,又接一柱,一連7柱,幾與橋邊護欄同高,水柱漸漸向橋身移近,「嘩啦」一陣作響,水柱登時傾圮,而橋欄上則俯臥著7口滅頂的人丁──正因肚腹給那欄杆抵著難受,嘴裡便大口大口嘔吐著泥漿水了。
此時橋當央那白袍少年又向河說道:「汝好生不殺,我佛自會勾記你一筆。若是先前被人攪擾,有個什麼閃失跌損,我倒是可以在汝衝霄凌雲之際,幫上一點小忙。如何?莫羞怯,汝且來!」
這時,原本萬里無雲的一片朗朗青天忽然打從正中央的所在,裂開一條大縫兒,烏雲從中滾出,如吹如注,黑色的霧氣稍一渙散,那蠶豆般大的雨點兒便串成千萬條鞭子似地捶撻下來。雨水落入河面,卻像在剎那之間變成了黏稠不堪的膠質,不時在河面上牽扯起一片簾幕一般的黑色水牆──不不不,不是水牆,被雨水從河中牽拽出來的,居然是一片3丈來寬的尾巴;光是寬,就有3丈,可知這尾巴少說也有1里多長了。
此龍由尾至頭而出,最後龍頭出水之時彷彿打從河底冒出一座山的模樣。山上當然少不了頭角鱗甲,光焰赫赫,才拔起來約莫2、3里許之高,又低頭俯衝而下,直向橋上的白袍少年衝去。那白袍少年一不躲避、二不抗拒,端端是一副任撲任咬的神情。河龍倒也乖覺,每俯衝一程,身形就小了一半,轉瞬間打從半空裡來到白袍少年的頭頂,居然只餘尺許長,「啪嗒」一聲,掉進缽兒裡,不過3寸有餘。
「風停雨歇之時,劫難開過,黎庶無咎,此後再無羈身之事!」白袍少年將手伸進缽兒,抓條泥鰍一般地抓起那河龍,另隻手將空缽朝眾人一傾,缽兒穩穩當當地放在橋欄頂端,他和那河龍卻一齊消失不見了。風雨乍停的晴空之中傳來一聲佛號,接著,是一段如經似偈的話語:
爾時。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共復一形。涕淚哀戀。白其佛言。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但於佛法中所為善事。一毛一渧。一沙一塵。或毫髮許。我漸度脫。使獲大利。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慮……佛贊地藏菩薩言。善哉。善哉。吾助汝喜。汝能成就久遠劫來。發弘誓願。廣度將畢。即證菩提。
菩薩留下來的,不過是個斤把重的銅缽兒,缽兒就搖搖墜墜放置在橋欄上,可恁是誰也動彈不得。然而某日來了個乞丐,隨手一抓便取走了。有個船夫在一旁瞧見,覺得很不尋常,跟著那乞丐穿街過巷,偶一失神,只見那乞丐居然走進一堵牆裡去,不見了蹤跡。
往後這乞丐經久不曾現身。直到某一日,這個盯梢的船夫在洗馬橋頭繫纜索的時候,猛裡一歪身,倒在碼頭上死了。怪的是,空船的纜索逕自鬆解,船頭調轉回西,沿著浣紗河順流而下,直漂到武林門,才忽然在河當央停住,連打了2、30個鏇子,這時左近幾里之內閒慌無事的船夫也都打陸路水路上趕了來,眾目睽睽之下,艙棚裡晃晃悠悠走出來一條漢子,一邊兒揉著惺忪的睡眼、一邊兒說:「藏王有旨:該幹活兒的就幹活兒去,這船歸我、篙子歸我、櫓子歸我、缽兒歸我──還有這藏王的勞差苦力也一總歸了我啦!」話說完,眼一睜,彷彿不知道自己先前說了些什麼,踉踉蹌蹌站穩了,脫口大叫:「誰把我搖過河來啦!快搖我上去啊!」
此際在河在岸的船夫早將這漢子團團圍住,忽而有人大喊了一聲:「他就是拿走那缽兒的花子!」
這個花子,就是杭城首任的「藏王」──清湖幫、運河幫兩幫船夫的共主。至於第五明是第幾任?沒人數得清,只知道他和歷任的藏王差不多,原先都是不肯幹這差使的。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電台主持人。曾獲聯合報小說獎、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小說《南國之冬》(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