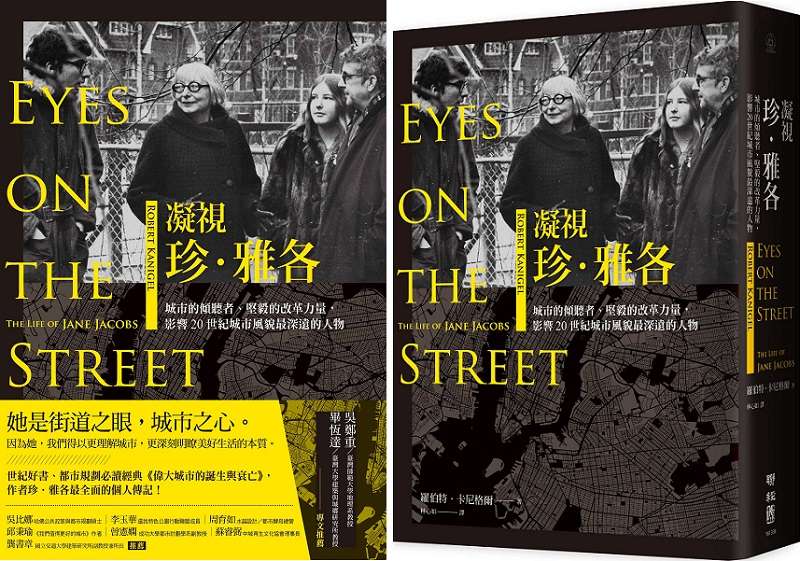請給我一個閱讀厚達六百頁傳記的理由。理由無他,因為她是珍‧雅各(Jane Jacobs)啊!
珍‧雅各是何許人也?基於她在城市與經濟思想上的巨大貢獻,在她死後,美國與加拿大都明定了「珍‧雅各日」(Jane Jacobs Day)、幾十個國家的城市定期舉辦「珍散步」(Jane’s Walks)的活動(以徒步或騎腳踏車的方式來探索地方鄰里)、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珍‧雅各獎章(Jane Jacobs Medal)(以表彰對都市設計有卓越貢獻的人士)、谷歌(Google)在她百年誕辰當天以她做為搜尋引擎頁面的主圖像。
如果你讀過由誠品書店選為百大經典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你會好奇,是怎樣的人生經歷與學術訓練,讓她可以寫出這樣的經典?如果你不認識她,你會好奇這位成長在美國長春藤盟校還拒絕招收女學生的年代,只有高中畢業,卻能夠與撰寫《寂靜的春天》的瑞秋‧卡森以及《女性迷思》的作者(也是婦女運動的推手)貝蒂‧傅瑞丹齊名的偉大女性,究竟是怎樣的一號人物?
珍‧雅各的父親是醫師,母親曾經擔任小學老師與護士。她從小受到父親很深遠的影響,喜歡查閱百科全書。父親告訴她,不要輕易許下自己無法實現的諾言,尤其是「我這一輩子(the rest of my life)都……」這種要賭上一生的。小學時,有次老師要同學們承諾從今以後每天都要刷牙,珍‧雅各就不舉手,還說服同學不要舉手,結果被老師趕出教室。她痛恨學校教育,高中畢業就急著去工作,想要寫作或當記者。父親認為應該先學習一技之長再上班,於是她便去學了速記(那年代還沒有錄音機)。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某小報婦女版編輯的無薪助理。
十八歲時,珍‧雅各到紐約尋找工作機會,住在姊姊家(位於布魯克林皇冠高地)。有天,她在曼哈頓搭公車,受到站名克里斯多福街(Christopher Street)吸引,下了車,自此愛上格林威治村。這裡有吸引人的建築、蜿蜒的馬路,有市場、書店、咖啡館、劇院、修鞋店,是很有創造力的鄰里。她覺得這才是適合定居的場所。後來她憑著速記能力在一家公司擔任秘書,便搬到格林威治村居住。那幾年她經常探索、觀察、描繪紐約的鄰里。《時尚》雜誌還刊載過一些她的文章,當時一篇文章的稿費相當於她一個月的薪水。她從觀察人孔蓋(上面的文字)進而研究其下(紐約地下世界)管線的運作。
(相關報導:
死守製造業的城市,必然衰敗:珍雅各《城市經濟學》選摘(2)
|
更多文章
)
當時哥倫比亞大學還沒有招收女生,想要回到學校進修的珍‧雅各只能選讀推廣課程。她修了地質學、化學、動物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成績很好,然而她並沒有取得大學文憑。她二十五歲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書:《制憲遺緒》(Constitutional chaff: Rejected sugges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後來,她到《鋼鐵紀元》(The Iron Age)雜誌工作,撰寫文章。有鑑於自己的家鄉史卡蘭頓的礦產關門,二萬多人失業,數千家庭外移尋找其他工作機會,家鄉有可能成為鬼城,她撰文討論這個問題,引來各方關注,政府也因此將(服飾、背包)工廠設置在此,增加許多工作機會。但即便珍‧雅各如此有能力,雜誌社老闆卻認為她是麻煩製造者。在性別歧視嚴重的當時,她曾因為女性薪水只有男人的一半,組工會爭取工人的權益。一九四三年,珍‧雅各轉換跑道,進入政府單位(戰時情報局)工作,這單位成立的目的是鼓勵愛國心、說服美國人參與二次大戰。此辦公室於一九四五年收攤後,她轉往另一政府部門發行的《亞美利堅》(Amerika)雜誌工作,宣揚美國的民主來對抗共產獨裁,寫的文章被翻譯成俄文,以對俄宣傳。
二十八歲時,她與建築師鮑伯‧雅各結婚,在格林威治村買房。這地方有各種族、不同背景的居民。有了兩個兒子後,母親的角色又讓珍‧雅各有了不同的觀看城市的觀點。這座城市會是一個有活力而安全的地方嗎?一九五二年,她轉到《建築論壇》(The Architectural Forum)雜誌任職,開始撰寫有關建築、都市計畫的文章。戰後,大量少數族裔搬遷進都市中心來找工作機會,居住在擁擠、條件很差的環境裡。政府開始大規模都市更新,清除舊房,興建高級華廈、劇院、政府辦公大樓,也為貧窮者興建國民住宅(現代主義風格的高樓)。當時《建築論壇》雜誌非常關心以下諸問題:什麼是都市更新與重建美國城市的好方法?人們應該住在高層還是低層的建物?都市空間要如何安排,讓小汽車得以通行?商業與住宅空間的關係為何?珍‧雅各後來到費城、波士頓參訪,看到了舊社區的活絡與多樣,以及新高層國宅的單調與危險。當時超大街廓的國宅,缺少轉角的報攤與雜貨店(這些商店可以聯絡社區感情),高樓層則阻礙了家長關照遊戲的兒童,犯罪的危險讓人更不敢出門。
一九五六年,《建築論壇》雜誌編輯臨時無法到哈佛大學演講,請她代打,她勉強答應,結果演講空前成功。她批評都市規劃師偏愛單調無聊的超大街廓高層國宅,卻不喜歡沿街的低矮建築,認為如果沒有糖果店、小飯館、洗衣店這些居民可以碰面的地點,居民就更難有機會相遇。都市計畫將傳統物理社區剷除的同時,也會將社會社區一併剷除。當時《財星》雜誌的編輯懷特(William F. Whyte)就坐在台下,深受她原創的想法吸引,便邀請她為《財星》寫一篇專文。然而雜誌社的其他工作人員卻抱持保留態度,認為一個騎腳踏車上班的女人,沒事的時候在鄰里搞社會運動,從沒寫過一篇偉大的文章,恐怕無法擔當此大任。一番波折後,她寫就了名為〈市區是為人民而存在〉(Downtown is for people)的文章,強調都市之所以有趣就在於豐富的街道生活。她宣稱都市規劃師所推動的開闊、公園式的、不擁擠的、對稱、有秩序的空間計畫,其實就跟墓園一樣。舊都市中心也許有些髒、有些醜,但是大規模的空間計畫會摧毀街道。洛克菲勒基金會希望她可以將此文擴大成為一本書,給她經費,可以暫時不用工作來寫書,而藍燈書屋(Random House)的著名編輯也承諾幫她出書。
摩西斯擁有權力且傲慢,持續開闢快速道路、橋樑、公園,興建聯合國總部,讓汽車族可以住在郊區,到市中心上班。任何擋在他計畫前面的,都將遭他摧毀。他認為讓不斷增加的汽車的快速移動,值得付出摧毀舊有社區當作代價。摩西斯認為要解決汽車的問題就要拓寬馬路,但珍‧雅各認為道路愈寬汽車就愈多,雙方各持己見,而面對珍‧雅各率領的抗議人士,摩西斯甚至在一次在會議上大吼:「其實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反對這個計畫,除了一堆媽媽們!」快速道路的興建案被成功擋下來了,珍‧雅各也成為著名的社區領導人與公眾人物。後來,她又成功阻擋了哈德遜街削減人行道寬度以拓寬車道的計畫(她就住在那條街上)。
一九六八年,珍‧雅各因參與反越戰示威而入獄,之後為避免兒子遭徵兵到越南打仗,舉家搬到加拿大多倫多。在那裡,她又遇到興建快速道路計畫,再度聯合市民將其擋下。在加拿大,她一方面持續參與社區運動,一方面寫作不輟,出版了好幾本重要書籍。
如果摩西斯(見圖)是從鳥瞰的角度觀看都市,把都市當作一張平面圖在其上任意揮灑;那麼珍‧雅各就是站在地面,從人群之中體驗都市。(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如果摩西斯是從鳥瞰的角度觀看都市,把都市當作一張平面圖在其上任意揮灑;那麼珍‧雅各就是站在地面,從人群之中體驗都市。她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提出「街道芭蕾」與「街道之眼」的概念,經紐曼(Oscar Newman)的《防禦空間》(Defensible Space, 1973)發揚光大,隨即開啟了「以環境設計防治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這門學科領域。她主張土地混合使用、高密度、新舊建築並存,幾乎與當時的主流都市計畫理論背道而馳。多數讀者稱讚她的想法原創、深具啟發、挑戰性。當然也有批評者認為,她只是想要複製格林威治村、太過羅曼蒂克、缺少對於權力結構的分析。她在另一本著作《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城市,是經濟發展的溫床》則大膽提出城市先於農村的論點,她所強調的創新,在知識經濟盛行的當代,仍有相當啟發。
珍‧雅各著作的中文出版,臺灣目前共有三本,包括《經濟就是這麼自然:聰明婆婆的經濟學講義》(先覺,二○○一)、《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聯經,二○○七),以及《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早安財經,二○一六)。事實上,早在「六一二大限」1之前的年代,建築學者漢寶德在一九七三年編輯的《環境心理學:建築之行為因素》(境與象出版),就選了兩篇珍‧雅各的文章,分別是〈人行道的利用:安全〉與〈人行道的效用:吸收兒童〉。四年級世代的建築系學生都深受其影響。
珍‧雅各傳奇的一生,值得人們細細品味。有人將之寫成歌劇、拍了紀錄片、繪寫兒童繪本、出版有聲書,更不用說還有很多人爭相為她作傳。
這本《凝視珍‧雅各》,有何特殊之處?珍‧雅各生前拒絕過很多記者為她出版傳記,但《凝視珍‧雅各》獲得雅各家族授權,作者得以訪問她的家人,獲得許多私密資料,還調閱了美國聯邦調查局二百多頁的相關檔案,得以近距離描繪這位奇特人物的家族史、在家中餐廳的談話,以及周遭人士對她的感受與評價。
想親炙這位思想家與社會運動者的精彩人生,這本書值得閱讀與珍藏。
凝視珍‧雅各:城市的傾聽者、堅毅的改革力量,影響20世紀城市風貌最深遠的人物(正書封)(聯經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