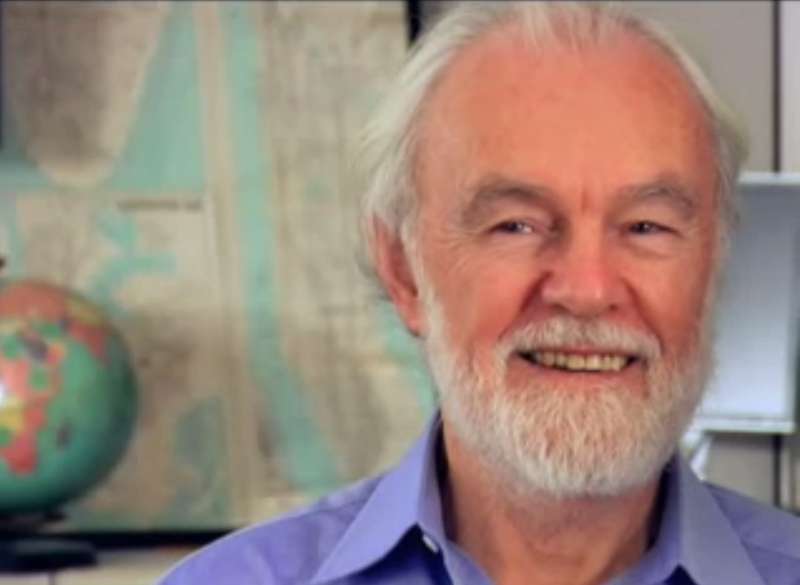位於台南市南區,一處廣袤且魚龍俱寂的城市墓地,看似是一塊再普通不過的荒蕪公墓,實則其中蘊藏的不單只是無數府城家族先人的安葬之處,同時也是數不盡府城人對其過往歷史記憶的捕捉地所在。而對雖出生成長於屏東,卻於台灣各地社區歷史深感興趣的筆者而言,更是一塊得以探求平時只短暫閃現於書本一隅的台灣先民歷史圖像之地。
對於生長於當代的我們來說,抑或是對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來說,每一塊留存過往記憶的空間景象都是無法失去的。然而,自台南縣市合併以來,市府便以配合道路、停車場、公園開闢及竹溪整治相關工程等理由,辦理了約4公頃的公墓遷葬。而後又以南山公墓緊鄰住宅區,影響當地居民生活環境品質,且設置於西元1984年的南區殯儀館已達飽和等為由,規劃設置了新的殯葬專區。在2018年8月8日的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官網最新消息更是提及了:
……公墓變公園固然大幅改造了城市景觀,但民政局期待本市南山公墓的遷墓可以達到更大效益。除改善市容觀瞻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外,更能以現代化建築設計以及一條龍之治喪流程,打造更符合人性尊嚴之殯葬專區,提升殯葬服務品質。
雖然在新任市長黃偉哲上任後,提出了將會依照文化資產法規定妥善辦理,必定會同時兼顧文化資產保存及都市發展兩大原則,但連署保存南山公墓的民間社團及文史工作者們,仍舊擔心市府只是形式上進行文資審查程序,時間到了依舊會將該地進行開發……。
歷史空間的他者化:巨大景觀積聚的資本社會空間
當台南市政府提出要使南山公墓遷葬發揮更大效益的論述(現代化建築設計、一條龍之治喪流程)時,極為明顯地,在塑造城市空間規劃的工程中,市府是以「資本創造」作為其最主要之考量。然而,在都市計畫的空間想像中,難道主持計畫者只能以資本與效益作為核心目標去進行努力嗎?對此,著名都市社會學者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曾於其著作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提及:
如果城市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世界,那也是他此後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間接地,而且在對他的工作沒有任何清楚覺察下,人類在創造城市的時候,也重塑了他自己。
當人類在創造一座城市時,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就等於是在重塑自己對於個人、群體、社群和社會的塑造與想像。然而,在當代發展主義下的台灣社會,大多數公民卻往往都將此創造城市及塑造自身的權利,讓渡給了「地產擁有者」、「地主開發商」、「金融資本家」及「國家政府」。將打造自己城市的權利,轉移至資本持有者的手上,將城市規劃,此一原應富含有豐厚人文精神與人道主義的工程,轉變為「資本主義對自然和人文環境的擁有」,此不正是在工業化資本主義氾濫的時代下,台灣社會單向度的根源嗎?
(相關報導:
台南美食真的吃不完!精選10間「必吃傳統小吃」CP值爆高,光看照片就猛流口水啊!
|
更多文章
)
就如同英國哲學家柯靈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曾在其著名歷史哲學著作《歷史的理念》中所提及的:
人類渴望了解萬物,也渴望了解自己。不了解人本身,人對其他事物的了解必無法完整。因為了解某一事物,但卻不知道自己,了解此一事物只能算是一知半解。自我了解對於人類而言不僅有其價值,亦有其重要性。這價值與重要性不只針對人類而已,而且也是批判其他知識或是使其他知識具有紮實根基的先決條件。
歷史作為人類了解自身最重要的基礎根源,記憶作為個體中介於群體之間最重要的根本媒介,如果要依照它們最真實的面貌來認識它們,空間歷史遺跡的景象就必然不可缺少。歷史既出現於時間,也停頓於空間,位於台南市南區的南山公墓,承載的絕不只是所謂台南「歷史名人」的記憶與墓碑而已,其更為重要的是它保存了無數府城人對於其家族歷史過往真實記憶的歷史景象空間,而這不正也是活於當下的我們見證與捕捉流逝過往歷史的最佳媒介嗎?
英國哲學家柯林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認為,自我了解對於人類而言不僅有其價值,亦有其重要性。這價值與重要性不只針對人類而已,而且也是批判其他知識或是使其他知識具有紮實根基的先決條件。(取自維基百科)
多向度的府城:關係空間下的異質地方
歷史塑造了空間,但歷史卻也同樣被空間所塑造。歷史空間作為歷史的產物,其承載的絕不僅是純粹物質性的地理疆域,而是還包含了豐富精神情感的感性心靈所在。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在其地理學名著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中提到:
如果我們認為空間是絕對的(absolute),它就成為一個「物自身」(thing in itself),有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於是,空間擁有一種結構,我們可以用來替現象分類歸位或是賦予個性。相對的(relative)空間觀則認為,空間應理解為物體之間的關係,其存在只是因為物體存在且彼此相關。有另一種意義的相對空間觀,而我決定稱之為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依照萊布尼茲(Leibniz)的方式,空間被認為包含在物體之中,亦即一個物體只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呈現了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時,這個物體才存在。
在某個空間點上的事物或發生過的事件,絕對無法僅僅訴諸於那個點上存在的事物來理解,它必定還取決於環繞著那個點的其他一切事物。而也就是那其他的一切事物與該空間的關係,決定了這個空間點的性質,以及生活其中人們對於此關係空間場域的社會構成連結所在。
當一個政府對於社會的治理愈是理性、技術性和工具性時,就愈難以想像被該政府治理社會中的城市(或生活其中的人們)如何才能夠打破其管理規劃的從屬狀態並進而獲取自身的解放。當我們的政府對於都市的想像建立在效益之上時,當我們的社會將對於自身都市的集體記憶主導權轉移至國家權力的支配時,我們又還能保有什麼歷史文化資產?我們所建構的空間,又怎麼才能具有歷史、記憶與生活的向度呢?
在某個空間點上的事物或發生過的事件,絕對無法僅僅訴諸於那個點上存在的事物來理解,它必定還取決於環繞著那個點的其他一切事物。而也就是那其他的一切事物與該空間的關係,決定了這個空間點的性質,以及生活其中人們對於此關係空間場域的社會構成連結所在。圖為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取自維基百科)
被涵化的人民?資本結構中的台灣民主社會
二十世紀英國著名的文化理論家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曾在其重要文化研究理論著作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中對於文化(Culture)一詞的歷史語意有過詳細探討。他提到:
文化(Culture)在所有早期的用法裡,是一個表示過程(Process)的名詞,意指對某物的照料,基本上是對某種農作物或動物的照料。從十六世紀初,「照料動植物的成長」之意涵,被延伸為「人類發展的歷程」。直到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初期,除原初的農業意涵外,這其實就是文化的主要意涵。
由此,相信讀者們可以了解到,文化(Culture)一詞其最核心的意義其實就是「對人類發展歷程的過程演變史」。如此,見證了數百年來無數府城先民生活經歷、生離死別、逝者與生者記憶的南山公墓,又怎麼會算不上是一塊值得我們好好保存的文化遺址呢?
然而,握有公權力及宣傳工具的政府及政治人物們,卻透過傳播媒介告訴人民,該地需要被整治與開發,如此地方才會繁榮,居民生活品質才得以提升。此不正如同傳播批判理論中所提到的,「媒介被視為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環,最終的控制權則逐漸集中在壟斷的公權力與資本利益手中」,人民的思想、言說及行動,也就在這個資本結構下的台灣民主社會,被逐漸涵化(Cultivated)為與主流意見相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