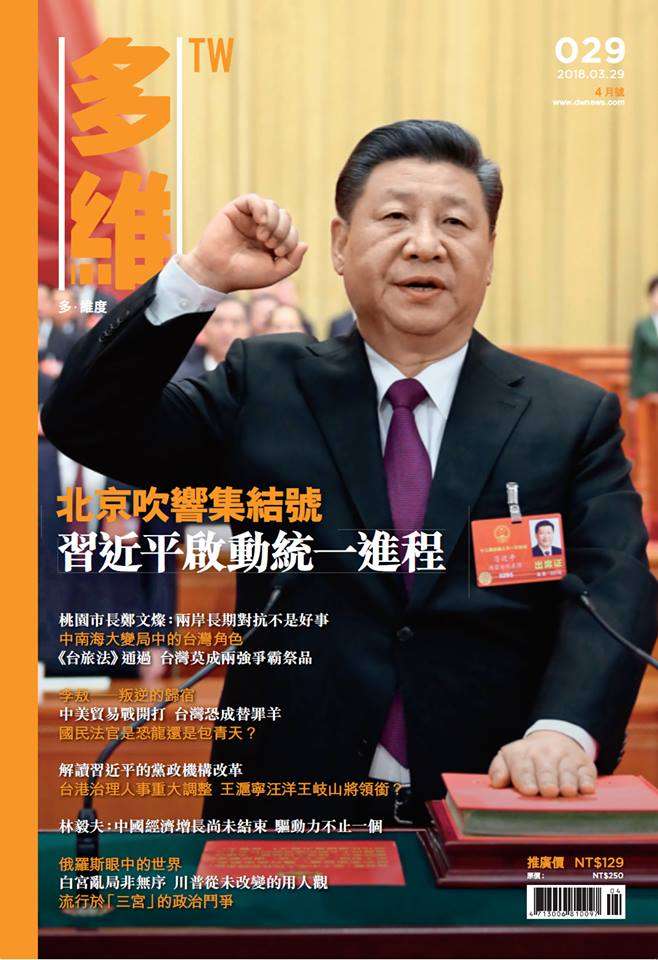終於,在美東時間3月16日,《台灣旅行法》(簡稱《台旅法》)得到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簽署通過。台灣官方、學者及各大智庫,對此多數認為此法案通過為「自從《台灣關係法》之後,台美關係間最大的突破」。紛紛以此為台美關係熱絡、活躍的契機,是台灣重大的「外交突破」。事實上,若我們觀照台美中關係近20年來的演變,以及《台旅法》立法前後的因果,或許就能知道,事情遠非台灣內部單方面所想的那般單純。
台美中關係 20年回顧
我們回顧近20年台美中關係,美國台僑團體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就不斷遊說、推動的《台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在2000年被當時的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否決,官方理由是「此法案如果通過,不僅不會增強台灣安全,還可能將威脅美國、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微妙平衡,甚至可能造成亞太地區動蕩不安」。
美國台僑團體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就不斷遊說、推動的《台灣安全加強法》,在2000年被當時的總統柯林頓否決。(資料照,美聯社)
而在2000年,即使美國否決《台灣安全加強法》,當時華府菁英階層對「圍堵中國」的氣氛猶有餘溫。其一是「1996年台海危機」陰影剛去不遠:其二是當時中國大陸解放軍還未成為「藍海」軍事強權,解放軍的海空軍實力仍老舊落後。
即便如此,昔日2001年4月1日發生「南海撞機事件」,華府的「主戰」聲浪雖強,但剛執政的小布希(George Bush)政府,還是選擇與中國大陸談判,謹慎地將此事政治負面效應減到最低。也就是說,即使當時解放軍並未擁有「藍海」軍事能力,但美國的顧慮已是千絲萬縷,圍堵中國是一回事,但實際進入衝突則是另一回事。
南海撞機事件後不久,美國便因為「9·11」事件進入了21世紀初的「反恐戰爭」時代。因為「9·11」,美國戰爭機器短時間內轉變成「反恐」效能,美軍的戰略也從模糊的「圍堵中國」,技術性地轉彎到反恐戰場。為了能在中亞、中東地區反恐,美國不得不走回冷戰末期雷根(Ronald Reagan)時代的拉攏中國老路。由於反恐戰場的轉換,美國需要中國大陸在中亞、中東甚至非洲地區與美國合作。
反恐10年後的2010年,中亞、中東的反恐戰場戰火不歇,且牽涉各國政治槓桿角力的因素日益複雜,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在不斷擴大反恐戰場的難局中,驚覺美國在東亞的政治真空狀態已瀕臨界點,故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大戰略,所謂「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目的,即是為壓抑在亞洲迅速崛起的中國大陸,故歐巴馬政府將亞洲地區成為美軍力量最強前沿。
「重返亞洲」以失敗告終,而川普鑒於「軍事過硬」無法在東亞局勢中佔到便宜,故在其「美國優先」的意識形態指導之下,改用以「貿易戰」取代軍事部署,這場中美貿易戰即將開打,20 年前認為「美國必須圍堵中國」的華府菁英階層中,已經開始擔心「中美貿易戰一起,美國不可避免要使用台灣牌,這對台灣本身將是危險之舉」。而《台灣旅行法》就是在這樣的美中關係格局下走上台前,推出這一法案的根本目的,是美國為了因應中國大陸崛起,試圖用台灣牌來遏制中國,並作為在經貿上勒索中國大陸的工具,並不是美國菩薩心腸,想要維護台灣的國際利益。
因為911事件,美國戰爭機器短時間內轉變成「反恐」效能,美軍的戰略也從模糊的「圍堵中國」,技術性地轉彎到反恐戰場。(資料照,美聯社)
陸反應冷淡 另有玄機
《台旅法》事實上並非新鮮事,在2016年9月在參眾議院就已經被提出過,2017年的1月和5月再度提出。經過冗長的議程,終獲川普簽署通過。看似台美政府的高層官員從此可自由來去互訪,甚至台灣的內部認為「美國透過立法,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國家看待」。果真如此,為何此「茲事體大」的法案通過後,不僅美國官方冷靜以對,僅有親台前任政客和掮客大做文章,而中國大陸官方也是異常冷靜,僅用「照本宣科」方式重申數句官式語言,就不再有進一步發言。美、中的異常「冷靜」,配上台灣內部「風風火火」的激昂,箇中是否另有玄機?
按照國際政治的邏輯推演,川普最後一刻才慢吞吞簽署此法案,在這段時間裏,中、美之間難道沒有進行某些談判甚至協議共識?在美國國會民意的大勢所趨下,中共官方知道恐難以「硬阻擋」,故很可能採取別的方式來解決。對美國在大戰略環境下「非做不可」的背景原因,雙方或已存在某些默契。
通盤觀之,台灣問題雖然是中美間的「火藥庫」,卻不是近期最重要問題。習近平剛完成軍改、政改和確立內部領導地位,台灣已經是其囊中物,是隨時可解決的問題,主導權在中國大陸手上,要不要發動攻勢?何時、何處、如何發動?都在中國大陸掌握中,處理台灣問題的「最後一里路」,就是「搞定美國」。一旦中美基於更大目標、達成戰略性合作與和解,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而言,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小菜一碟。而大陸官方為何緩慢出手、手中有多少牌?這才是「冷淡回應」中的「熱點」。
雖中國大陸官式回應「低調冷淡」,但言語間提到了「挾洋自重」,這對台灣是非常大的警訊。所謂「兩隻大象打架,遭殃的就是腳邊的小草」。台灣面對兩大強權競合戰略遊戲,如果輕易地選邊站或輕易相信一些簡單得到的好處,後果就是在強權相爭的大局下,將自身剩餘價值用到盡頭。
全球新局下《台旅法》價值幾何
從2010年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戰略,受到中國大陸急速崛起態勢而受挫後,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受到來自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挑戰,而成為「多極世界秩序」的可能已經存在。有美國學者稱「歐巴馬政府直到最後一刻,依舊仍不願意相信克里姆林宮準備崛起」的現實,故在中東、特別是敘利亞戰場進退失據。而在歐洲,也因美國維持「單極世界秩序」面臨挫敗,在國際間的公信力喪失,故歐盟有「歐洲聯盟軍」(EUFOR)的設立,就是為了避免美國臨時抽腿,所聯合起來的「自保」舉動。
(相關報導:
《台灣旅行法》過關》陸媒:美國國會衝動、好鬥達到沸點,中國要把台灣打成一桌亂牌
|
更多文章
)
在東亞面臨失敗的「重返亞洲」戰略,由川普政府以發動「貿易戰」為主軸的戰略繼續進行維護「美國利益」的鬥爭。但是打著「美國優先」的商人總統川普,其政治決策能力搖擺不定,又缺乏傳統「建制派政客」的穩固官僚性格,在東亞也讓日本驚覺到「被川普政府邊緣化」,如突然出現的「川金會」,讓東亞新格局突然轉向,日本感受到遭背棄的滋味,故安倍政府在2018的《四年度防衛大綱》提出前,大舉增加防衛預算、購買更多戰機、航母計劃等,都是因為川普的政權「極度不穩固性」所導致的「自保」轉變,這與「歐洲聯盟軍」的成立如出一轍。
如今,北韓核武問題極可能在「川金會」後得到解決,幕後功臣眾人皆知,就是中國大陸。而對於中國來說,在其周邊格局中,原本只有北韓和台灣問題無法掌控,可能會帶來衝突風險。但北韓問題和平解決後,其戰略重心,將會向東南方向的台灣發力,這種置千鈞於一點的態勢,恐怕是台灣所難以承受的壓力。也將讓所謂《台旅法》的利多態勢,迅速豹變為台灣手上的燙手山芋。
台灣須做關鍵抉擇
不論是從歷史或現今的國際格局來看,台灣此刻都面臨抉擇的十字路口。若能從歷史觀之,朝鮮半島的問題,百餘年來都在關鍵時刻影響台灣,1894年的東學黨之亂造成台灣變成日本殖民地,1950年6月韓戰爆發,使得原本擬遺棄台灣蔣介石政權、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美國杜魯門政府,將亞洲戰力最強的太平洋第七艦隊主力,置放在台灣海峽,執行「台海中立化」的政策。這兩次發生在朝鮮半島上的變局,都影響了台灣的命運,也間接形成台灣目前的狀態,而如今,朝鮮半島可能第三次發生大變化,台灣是否能夠置身事外?或有能力選擇自己的道路?
台灣從韓戰後,一路都以「美國保證」作為護身符,無條件吸收來自美國的資金、軍火、意識形態和政治選擇,台灣雖自稱「獨立國家」,在國際眼中卻是不折不扣的「美國附庸」。即使面臨美國「放棄台灣」多次,台灣對美國的依賴依舊,無法脫離其戰略佈局的棋子身份。以台灣位居「太平洋第一島鏈關鍵地位」為思想中心,意欲達成那個想像中的、不可能存在的、以「台灣利益優先」的「美國戰略」。事實上,台灣已經吃過太多虧,禁不起一再被出賣。
台灣在東亞的關鍵地位,於地緣政治學上不言可喻。但是,這般的關鍵,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又何嘗不是?對台灣來說,在已經嚴重失衡的兩岸格局下,如果繼續遵從「美國利益」而說服自己那是「台灣利益」,而忽視整體東亞戰略格局已經改變,恐將為台灣帶來最大的災難。全球戰略格局正在重新建構,中美兩二大強權在東亞爭鋒,已屬必然,未來不論是「單極」抑或是「多極」世界秩序,台灣如果一再將自己綑綁在美國利益的戰車上,必將失去自主機會,等於直接放棄自我抉擇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