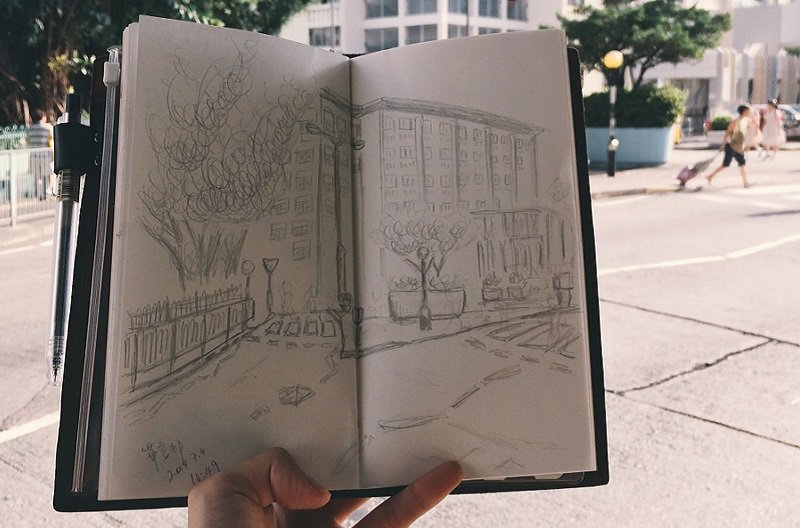升上中二,程緯發覺朱老師很欣賞他的作文,鼓勵他把文章投到《香港時報‧學生園地》,他第一次投稿就成功了。文章的題目是〈初春霧裏的大水坑〉,模仿朱自清的〈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筆法也學朱自清。中學語文課本裏多的是冰心、朱自清、徐志摩的詩文。為甚麼小學的語文課本,文章都沒有作者的名字?
介紹望夫石、紅梅谷的文章,是誰寫的呢?程緯開始問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朱老師是台灣人,粵語說得有點生硬。她教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程緯感到朱老師不喜歡日本。她說日本人非常殘忍,殺害了很多中國人。她批評《紅白歌唱大賽》不好看,日本歌「聲震震」不好聽。但程緯喜歡看《紅白歌唱大賽》。不久,他就碰到了「魚與熊掌」這個成語。課本選了《孟子》的篇章。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程緯想,怎麼又是引誘人死呢?他走到圖書館,看《論語》、《孟子》,抄下一些語句,半懂不懂地唸著。
中三作議論文,靈光一閃,他忽然寫下一句文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羅老師用朱筆眉批:「此乃孟子論大丈夫之語。」然而,程緯很快讀到魯迅的〈狂人日記〉。他在山邊書店買了厚厚的《魯迅小說集》,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記〉。他邊看邊用紅筆在新詞旁畫線,學了「發昏」、「青面獠牙」、「白厲厲」幾個詞語。他看不懂這篇小說,但他知道魯迅說仁義道德「吃人」。他感到迷惑。羅老師說:「寫議論文要用語例,你們記一些。」於是,他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寫,程緯一條一條地抄:(1)《左傳‧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2) 英國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說:「死水有毒。」
這是程緯第二次讀到外國詩人的名字了。去年,剛從中大英文系畢業的郭Sir,當上了他們的班主任。郭sir熱愛文學,和他們談余光中、張愛玲、巴金,還訓練全班學生在周會集誦美國詩人Robert Frost的The Road Not Taken。程緯除了知道有兩條路,就不知道這首詩講甚麼,只能死背,跟著同學一起唸。他最熟的是開頭和結尾,朗讀得特別大聲:
(相關報導:
胡又天專欄:復興了粵語歌壇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上)
|
更多文章
)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一個女同學說:「你喜歡寫作,不如參加青年文學獎。」程緯聯想到諾貝爾文學獎,回了一句:「我哪有資格參加?」後來他看到山邊書店附近的牆壁貼著青年文學獎的海報,原來已是第六屆。他參加了初級組散文、新詩。在「投稿者座談會」上,他見到一個評判,叫蔡炎培。他看課外書,知道五四運動有一位領袖,叫蔡元培。香港竟然有一個詩人的名字,和五四運動的領袖,只差一個字!蔡炎培侃侃而談,說「滿月扶光」,才是詩的語言,說了一會就無端流下淚來了。程緯覺得莫名其妙,原來詩人是這樣的。頒獎禮結束後,他才知道自己的參賽作品全軍覆沒。但他很開心,他原以為作家都是在課本上的,而且都是死人;原來香港也有活生生的作家,就在面前。慢慢的,他喜歡香港文學,多於五四文學,他知道誰是也斯、西西、黃國彬、何福仁。
中三下學期,程緯參加了中文寫作班。陳老師讀到他造的比喻句,十分欣賞。陳老師介紹他看《大拇指》, 他常常到報攤看《大拇指》出版了沒有。在蔡振興主編的《香港文學》上,他讀到劉以鬯的〈蜘蛛精〉,就試著寫了一篇評論〈評析劉以鬯的《蜘蛛精》〉,投到《大拇指‧書話版》,竟然刊登了。編輯迅清打電話約他在香大學見面,見到他,說:「竟然是個中三學生。」
後來他參加《大拇指》的活動,探訪編輯。他看到范俊風、馬康麗、肯肯;在一個文藝活動後,他在巴士上見到鄧阿藍,還和鄧阿藍說過話。程緯不斷寫作,不斷投稿。他投了超過二十篇習作給喜愛的文學雜誌《青年文學》,全部給投了籃。程緯在第七屆青年文學獎,終於得到他生命中第一個獎座──朱銘的「李白醉酒吟詩像」。
程緯愛上了文學,住在華珍樓的同學陳星也熱愛文學。但陳星的爸媽都不喜歡陳星看文學書、寫作。陳星說他的媽媽常常說,讀文學沒有用,中文好沒有用,讀文科沒有用;最重要還是英文好,最好讀醫,或者讀法律,做醫生,或者做律師。陳星說:「我要躲在廁所寫作,免得她看到又嘰哩咕嚕。」程緯沒有這種壓力,因為阿香、阿水不會理他的學業。他知道,爸爸非常努力工作,為了省錢,往尖沙咀返工,只會坐天星小輪,從不搭過海巴士;餓了連花生都捨不得買來吃,差不多把全部薪水交給媽媽,養活妻兒是他唯一的希望,人生唯一的意義,沒有娛樂,不談享受,不上茶樓,不看電影,不看書,不讀報紙,不關心社會大事;除了妻兒,阿水不能忘記的,就是故鄉的親戚,和血濃於水的鄉情。程緯想:一個人,可以不選擇這樣的人生嗎?中三了,數學、物理、化學,全部不合格。他想,或者升不上中四,要像姊姊輟學打工了。如果他仍然熱愛文字,就到報館執字粒;不然,到華富餐廳賣麵包。
新建的華景樓、華翠樓,旁邊的新街市,商店、攤檔越開越多,總會請人吧?兩年前,在電影院看《半斤八兩》,他看到許冠文把香腸當雙節棍揮舞,被人用巨大的鯊魚牙噬去一截,面對這個超現實的情景,他笑得氣都喘不過來;笑完,想一想,開開合合的鯊魚牙,在這個城市代表甚麼呢?程緯漸漸感到,《半斤八兩》的歌聲離他越來越近。沒書讀,自己會當「打工仔」吧?會「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像他的爸爸一樣?他開始喜歡這首歌。
程緯放學回家,總是見到阿香、阿金、姑姐等人攻打四方城。程緯已經不喜歡打麻雀,多少年沒見過星球人、阿發、布魯圖、潮州仔呢?程緯甚至有點鄙視阿香──只會打麻雀,只會寒著臉叫他喊人,或者在阿金、姑姐走後,罵他不喊人,別人以為她沒家教。程緯做功課的時候,聽到她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好像想說,又好像不想多說。他都聽出來了:原來多年不見的吳太,在澳門賭場輸了很多錢,問大耳窿借,又輸光,被人押回香港。她老公氣得離家出走了,一個扯皮條住在她的家中,她就在家接客還賭債。唸中學的大女要幫母親還賭債,也開始在家接客了。
程緯唸中一的時候,到過吳太的家,因為母親沒有為他留下鑰匙,他趕著換衣服上街,四處找阿香,找到華興樓。吳太叫大女在冰箱中拿一杯啫喱給程緯吃。大女把啫喱連同小膠匙遞給程緯,程緯說:「謝謝。」她轉身到露台,坐下,兩肘抵著方桌寫字。他吃著吃著,吳太的細女忽然拿著一杯清水給他看,說水裏有三條魚。程緯瞪大眼睛,左看右看都沒看見魚,就說:「沒有魚,只是一杯清水。」吳太的細女非常認真地說:「有呀!有呀!一共有三條,你怎麼看不見?」程緯說:「只是水。」細女走進廚房,倒掉杯中的水,把杯放在水龍頭下,扭開水掣,水嘩嘩注入杯中。細女把玻璃杯拿出來,又說:「你看,現在有四條!」程緯笑說:「水喉水不可能沖出魚來。」細女說:「真的有!嗱,你看,這裏有一條,那裏有一條,有一條魚游到水面上,那些魚很小很小的呢,你怎麼沒看見?」程緯給她弄糊塗了:她有透視眼,還是我的眼睛有問題?
(相關報導:
胡又天專欄:復興了粵語歌壇的毛記電視分獎典禮(上)
|
更多文章
)
*作者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著有詩集《樹根頌》、《尚未誕生》、《時間問題》;散文集《山水之間》、 《魚話》;小說集《魚咒》、《破地獄》、《蟑螂變》;評論集《余光中、黃國彬論》、《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本文選自多位香港作家合作之小說選集《年代小說.記住香港》(KUBRICK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