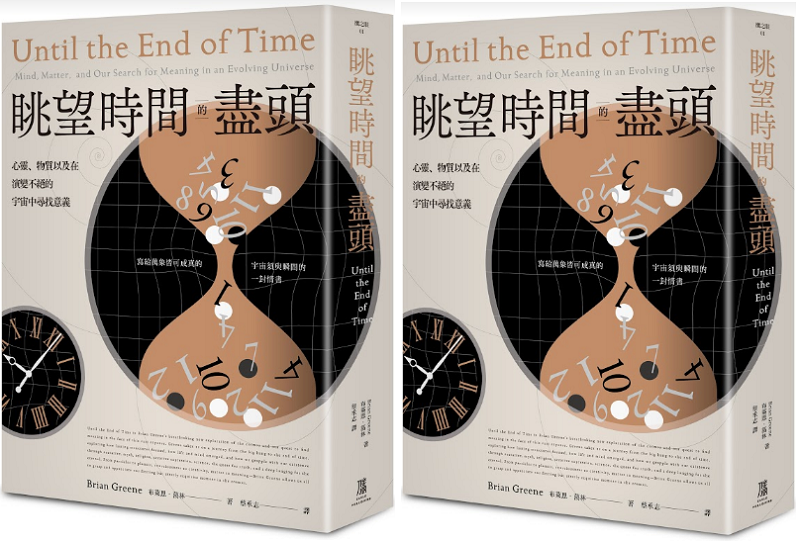過去與未來的差別既是基本的,也是人類經驗的樞紐主軸。我們誕生在過去。我們會在未來死亡。在這當中,我們目睹了無數起事件,而且是以一種系列狀況接續開展,倘若把這個順序逆轉, 就會顯得荒誕不經。梵谷畫下了《星夜》(Starry Night),接著就沒辦法逆轉運筆動作,把迴旋色彩移除,重現一張空白畫布。鐵達尼號擦刮冰山,扯裂船身,接著就沒辦法逆轉引擎,回溯它的航行路徑,並撤銷撞擊帶來的損壞。我們每個人都會長大變老,不過接著我們就沒辦法逆轉我們的內在時鐘並恢復青春。
由於不可逆性對於事物的演變至關重要,你應該會認為,我們很容易就能依循物理定律來確認它的數學根源。當然了,我們應該有辦法指出,方程式中有某個部分能確保事情可以從「這樣」 變成「那樣」;儘管如此,數學卻禁止它們從「那樣」變成「這樣」。然而好幾百年來,我們發展出的方程式,卻始終沒辦法為我們帶來類似那樣的結果。實際上,隨著物理定律不斷由許多人經手改良,包括牛頓(古典力學)、馬克士威(電磁學)、愛因斯坦(相對性物理學),以及促成量子物理學的好幾十位科學家,有一項特徵卻依舊保持不變:那些定律對於我們人類所說的未來和我們所稱的過去,始終堅守完全遲鈍不靈敏的特性。
基於世界現狀,數學方程式對於朝向未來或者過去開展的處理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儘管這種區別對我們很重要,而且具有深遠的影響,然而定律對這種差別卻嗤之以鼻,還評定它所帶來的後果不會比體育場用來計算用掉多少時間和剩餘多少時間的比賽計時來得更重要。這就表示,倘若定律容許事件依循特定序列展現,那麼定律也必然准許逆轉序列。
我在就學階段頭一次得知這點時,頓然覺得這簡直荒謬可笑。在真實世界當中,我們不會看到奧運跳水選手腳先出水從泳池冒出來,然後沉靜地翻落跳板。我們不會看到碎裂的彩色玻璃從地板跳起來,重新組合成一盞第凡尼彩玻鑲嵌燈(Tiffany lamp)。電影鏡頭倒帶播放之所以有趣,正是由於我們所見的播放影像和日常體驗的一切完全不同。然而根據數學原理,倒帶鏡頭逆向呈現的事件,卻與物理定律完全相符。
那麼,為什麼我們的經驗卻是這般偏頗?為什麼我們只能見到事件依循一種時間定向開展,卻永遠看不到逆向的情況?這個答案的一個關鍵部分是以「熵」的觀點來表明,而且熵這個概念會成為我們認識宇宙開展方式不可或缺的要項。
熵:初次相識
熵是基礎物理學中比較令人困惑的概念,這項事實並沒有減損自由引述它的文化胃口,大家依然喜歡藉它來描述從秩序到混亂,或者更簡單地說,從好到壞等日常狀況。按照口語用法這樣講也還好;我有時候也會那樣帶出熵話題。不過由於底下的行程得靠熵的科學概念來引領我們—也取決於羅素對未來的陰暗願景的中心思想—所以就讓我們梳理出它的比較精確的含義。 (相關報導: 搭乘旅遊泡泡首航班機回家 帛琉總統惠恕仁手比愛心:感受台灣滿滿的愛 | 更多文章 )
先從一個比喻開始。想像你猛晃一個袋子,裡面裝了一百枚硬幣,接著把硬幣倒在你家餐桌上。假使你發現所有一百枚硬幣全都正面朝上,想必你會大吃一驚。不過為什麼呢?道理似乎很明顯,不過也值得深思。連一枚反面的都沒有,意味著這一百枚硬幣各個都是隨機翻轉、碰撞並翻攪,最後還得撞上桌面並正面朝上就定位。所有硬幣都這樣,這很難辦到。要獲得那麼特別的結果是一項艱鉅任務。相形之下,倘若我們單只考量稍微不同的結果,好比結果只出現一個反面(另外九十九枚硬幣依然全都正面朝上),這種情況有一百種不同的發生方式:唯一那枚反面的可以是第一枚硬幣,也可以是第二枚硬幣,或者第三枚,並依此類推到第一百枚硬幣。因此,要得出九十九枚正面,比結果全都是正面容易一百倍—可能性達到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