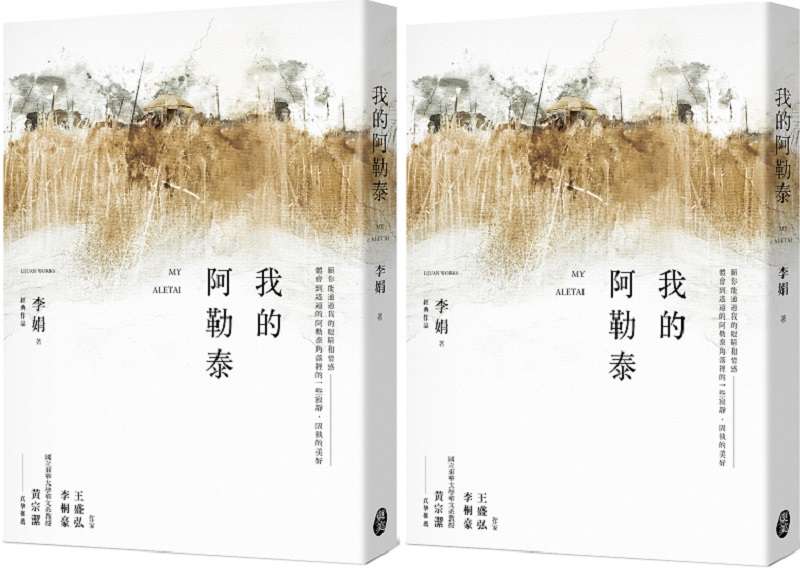早些時候,通往滴水泉的路只有「烏斯曼小道」。烏斯曼是一百年前那個鼎鼎有名的阿勒泰匪頭,一度被稱為「哈薩克王」。
而更早的一些時候,在這片茫茫戈壁上,所有的道路都只沿其邊緣遠遠繞過。那些路斷斷續續地,虛弱地進行在群山褶皺之中,遙遙連接著阿勒泰的綠洲和南方的草原雪山。沒有人能從這片荒原的腹心通過。沒有水,沒有草,馬饑人渴。這是一塊死亡之地。唯一知道水源的,只有那些奔跑在沙漠間的鵝喉羚與野馬,但它們不能開口說出一句話來。它們因為深藏著水的氣息而生有晶瑩深邃的眼睛。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就有滴水泉的傳說了吧?那時,只在牧民之間,寂靜而神秘地流傳著一種說法:在戈壁灘最最乾涸的腹心地帶,在那裡的某個角落,深深地掩藏著一眼奇跡般的泉水。水從石頭縫裡滲出,一滴一滴掉進地面上的水窪中,夜以繼日,寒暑不息。那裡有著一小片青翠靜謐的草地,有幾叢茂盛的灌木。水流在草叢間閃爍,淺淺的沼澤邊生滿苔蘚。那是一片狹小而堅定的沙漠綠洲──有人聲稱親眼目睹過那幕情景。當時他身處迷途,幾天幾夜滴水未進,已是意識昏茫,瀕臨死亡。然而就在那時,他一腳踩入滴水泉四周潮濕的草叢中,頓時感激得痛哭起來。他在那裡痛飲清冽的甘泉,淚流滿面。
每一個牧民在荒野深處尋找丟失羊羔的時候,都堅信滴水泉就在附近。也許就在前方那座尋常的沙丘背面?他四面呼喊,又饑又渴地走過一座又一座沙漠中的高地,墊足遙望。野地茫茫,空無一物。但他仍然堅信著滴水泉。
滴水泉如同這片大地上的神明。它的水,一滴一滴從無比高遠之處落下,一滴一滴敲打著存在於這裡的一切生命痕跡的脈搏,一滴一滴無邊無際地滲入苦寂的現實生活與美好純真的傳說。
然而戰亂使大地上不再存在安靜的角落。滴水泉最終還是從牧民世代口耳相傳的秘密中現身了。它的確切位置在戈壁灘平凡的遙遠之處被圈點了出來。烏斯曼的烈馬走出了一條忽明忽暗的道路,筆直地戳向滴水泉。那些烽火連天、濃煙四起的年月裡,烏斯曼一手持匕首一手握馬韁,無數次孤身前往這隱蔽狹小的綠洲,補充給養,休養生息。然後北上南下,穿梭戰事。滴水泉的隱秘在無形間造就了這個「哈薩克王」的神出鬼沒嗎?在當時,除了戈壁邊緣的官道以外,居然還有一條路也能使人在荒原上來去自如──這是烏斯曼的傳奇,也是滴水泉的傳奇。
圖為阿勒泰額爾齊斯河岸。(KING-FISH① - panoramio@維基百科)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還沒有現在的二一六及二一七國道線,從富蘊縣到烏魯木齊,也沒有開通班車(不過當時也沒有太多的人需要去富蘊縣。而生活在富蘊縣的人們,似乎也沒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離開)。要到烏魯木齊的話,只能搭乘運送礦石或木材的卡車,沿東北面的群山一帶遠遠繞過戈壁灘。一路上得顛簸好幾天。我永遠忘不了途中投宿的那些夜晚,那些孤獨地停留在空曠雪白的鹽鹼灘上的旅店,低矮的、破破爛爛的土坯房,還有房頂上空輝煌燦爛的星空。
(相關報導:
老闆要你推出自家的「冰桶挑戰」?品牌快速爆紅的新力量原則:《動員之戰》選摘(3)
|
更多文章
)
一次又一次,我被大人抱下車廂,被牽著往那裡走去。心中湧動著奇異的激動,似乎知道自己從此就要在這個地方永遠生活下去了。然而,我的命運直到今天仍沒有停止。
那條被稱為「東線」的漫長道路,只在夏天暢通。到了冬天,山區大雪封路,去烏魯木齊只能走通過滴水泉的那條路。
司機們路過滴水泉,無疑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無論當時天色早晚,都會停下來歇一宿。打水洗漱,升火燒茶泡乾糧。等過了滴水泉,剩下的路程又將是幾天幾夜無邊無際的荒涼。
後來,有一對夫妻從內地來到新疆,經歷種種輾轉後來到了滴水泉。他倆在泉水邊紮起一頂帳篷,開了一家簡陋的小飯館。所需的菜蔬糧油全都由過往的司機捎送。這樣一個小店對於司機們來說,簡直天堂一般。於是,在往返這片戈壁灘的漫長旅途中,總算能過上一天「人過的日子」了。
然而這對夫妻,他們在那樣的地方討生活,不只是辛苦,更多的怕是寂寞吧?常常一連好幾天,門口的土路上也不會經過一輛車。男的也常常會搭乘某輛路過的車離開一段時間。
再後來,多多少少發生了一些事情,那個女人跟著一個年輕的司機走了。那個男人也沒有等待,不久後也走了。滴水泉又恢復了深沉的寂靜。
不知又過去了多長時間,又發生了怎樣的周折,那個女人和那個司機再次出現在滴水泉。帳篷又重新支了起來,還挖了個地窩子(能住人的地坑,上面蓋有屋頂)。於是飯館重新開張了。泉水邊還放養了幾隻雞,簡陋的餐桌上出現了雞蛋和雞肉。
在這裡,司機們晚上也不用睡在狹窄的駕駛室裡了。新的小飯館還提供住宿的地方,雖然只是地窩子裡的一面大通鋪。
總會有一些時刻,大家都約定好了似的,突然間會有很多人同時光臨滴水泉。那時,飯桌前的板凳都不夠用了,吃飯時大家黑壓壓蹲了一屋子。睡覺的地方更是不夠用。女主人便把自己的床鋪讓出來,又把飯桌拼起來,還在地面上鋪上塑膠布和氊子。一屋子橫七豎八躺滿熟睡的身體。
就在那一年春天,從烏魯木齊到富蘊縣的班車正式開通,每星期對發一趟。班車經過滴水泉時,整車的旅客同樣會下車進食、休息。兩人的生意前所未有地興隆,滴水泉也前所未有地喧嘩。於是倆人決定把店面擴大。
整個夏天裡,當車輛改道穿行在東線的群山中時,滴水泉是悄寂無聲的。兩個人決定利用這段時間蓋幾間新房子。
他們把泉水下的水坑挖成深深的池子,又挖了引水渠一直通向店鋪門口。
泉水很小,他們用了一整個夏天的時間耐心地等待水池一次次蓄滿,用這些水和泥巴、打土坯。土坯晾乾後,土牆很快砌起。他們又趕著馬車,從幾百公里外拉來木頭,架了檁子、搭好椽木。最後在屋頂鋪了乾草和厚厚的房泥。
就這樣累死累活幹了一整個夏天,房子起來了,新的飯桌也打製好了,新床也添了兩張。他們坐下來等待冬天,等待第一輛車輛在門口鳴笛刹車,等待門簾突然被猛地掀開,等待人間的喧嘩再一次點燃滴水泉。但是,他們一直等到現在。
那些所有的,沿著群山邊緣,沿著戈壁灘起伏不定的地勢,沿著春夏寒暑,沿著古老的激情,沿著古老的悲傷,沿著漫漫時光,沿著深沉的畏懼與威嚴……而崎嶇蜿蜒至此的道路,都被拋棄了。它們空蕩蕩地敞開在荒野之中,饑渴不已。久遠年代前留下的車轍夢一般印在上面。這些路,比從不曾有人經過的大地還要荒涼。
新的道路如鋒利的刀口,筆直地切割在戈壁腹心。走這條路,只需一兩天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一切都在上面飛速地經過,不做稍刻的停留。世界的重心沿無可名狀也無可厚非的軸心平滑微妙地轉移到了另一面的深淵。
滴水泉的故事結束了嗎?滴水泉那些一滴一滴仍在遠方靜靜滴落的水珠,還有意義可被賦予嗎?從此再也不需要有一條路通向它了嗎?再也不需要艱難的跋涉和掙扎的生活來換取它的一點點滋潤了嗎?如今我們所得到的一切,全都是理所當然的嗎?
還有兩個人,至今仍留在那片小小的綠洲上。仍然還在泉水邊日以繼夜打土坯。並在等待土坯晾乾的時間裡,衝著天空仰起年輕的微笑的面孔。只有他們仍然還在無邊無際的等待之中,美夢絲毫不受驚擾。當我在這片荒野裡獨自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又走上了通往滴水泉的舊道。野地裡,路的痕跡如此清晰。不由得清楚地聽到那個女人的聲音。當她和她的情人無處可去、無可容身時,她勇敢地對他說:「我們去滴水泉吧!」邊說邊流下淚水。
蝗災
他們說蝗蟲來的時候,跟沙塵暴似的,半邊天都黑了。如烏雲密佈,遮天蔽日。人往重災區一站,不一會兒身上就停滿了蟲子,像穿了一身又硬又厚的盔甲。
還有這麼一個資料,說今年鬧蝗災的地區,最高蟲口密度為一萬五千頭/平方米。這也是我沒見過的。想想看,一個平方的面積裡居然能擠下一萬五千隻蝗蟲!那肯定是蟲摞蟲了,而且還會壘得很高很高。一個平方一萬五千隻!真噁心……他們怎麼算出來的?難道還一隻一隻地數過嗎?真噁心……
為了抵禦這場災害,政府號召災區群眾多養雞。有人告訴我,養雞滅蝗的事情還給編了新聞上了電視呢。畫面的大概情景就是:村幹部們全體出動,把一群雞從山上往山下呼呼啦啦地趕,雞們紛紛展著翅膀,光榮地浩浩蕩蕩衝向抗災一線。
說到養雞,想起了另外的一件事。十幾年前塔克斯肯口岸剛剛開關的時候,我表姐也去那裡做生意了。我和我媽便跟著去瞅了瞅熱鬧。在那裡,政府要求當地群眾積極參與貿易活動。提倡的辦法之一也是號召大家多養雞,因為雞下了蛋就可以用雞蛋進行邊貿互市了。另外,還可以把雞做成紅燒雞賣給外國人吃。不知道蒙古國那邊有沒有雞……
呃,回過頭來再說蟲災。那麼多的蟲,雞能對付得了嗎?一個個吃到撐趴下,也是趴在蟲堆裡吧?那麼多的蟲──每平方一萬五千隻……太可怕了。
不過用雞滅蝗好歹屬於生物技術呢。聽說還有的地方在噴藥。噴藥當然會更有效一些,但那麼做總讓人感覺不舒服:「藥」比蝗蟲更可怕吧?因為它實在太「有效」了,全盤毀滅一般地「有效」,很不公平地「有效」。
我們這裡的小孩子,釣魚用的餌全都是蝗蟲。不知道這有什麼好吃的,魚居然也能給騙上鉤。
我記得小時候,還在縣城裡上小學時,我經常穿過整個縣城去到北山腳下找一個叫燕燕的女孩玩。她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叫霞霞,一個叫明明。她家的房子很破,很空,但是很大。院牆從南到北、山上山下地圍了一大圈,差點兒就無邊無際了。她們的父母總是不在家,我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院子裡跑來跑去地玩。後來我們跑了出去,外面是成片的戈壁灘、起伏的粗礫沙丘。我們四處撿拾乾牛糞,拾回來可以當柴燒。因為她家很窮。窮人就燒這個,富人則一年四季都燒煤。我們去了很遠很遠,遠得快要回不來了。後來我們回來時,紅日懸在山頭,晚霞輝映大地。我們放下牛糞塊,開始捉蝗蟲玩。那麼多的蝗蟲,那個時候就已經有那麼多了。
──我們輕輕地走上前,輕輕地蹲下身子,突然罩上手,一下子就逮住了。捂在手心的蟲子仍虛弱地掙扎著。因為它是活的,有生命的,於是捏在手心裡總是令人異樣地興奮。它的腿能動,關節靈活;觸鬚雖然看來和麥芒一樣,但卻是有感覺的,是靈敏的,再輕微的觸碰都會使它迅速作出反應;還有它的翅子,那麼精巧對稱……對一隻蝗蟲仔細觀察,從尋常中看出越來越多的不可思議時,世界就在身外鮮明了,逼近了……我看到燕燕的眼睛閃著瑰麗的光。抬頭一看,緋紅的夕陽恰在此時全部沉落西山。天色迅速暗下來。一回頭,一輪大得不可思議的金黃色圓月靜止在群山之上。
蝗蟲是有罪的嗎?作為自然界理所應當的一部分,它們的種種行為應該在必然之中:必然會有蝗災出現,必然得傷害人的利益以維護某種神秘公正的平衡。當蝗蟲鋪天蓋地地到來的時候,我們為保護自己而使用的任何方法,其實也是對自己的另一種損傷吧?
唉,我們這個地方的農牧民真倒楣。不下雨的時候總是會鬧旱災,雨稍微一多又有洪災;天氣冷的時候有雪災,太熱了又有冰雹災;秋天會有森林火災,到了夏天呢,看看吧,又總是有蝗災。此外還有風災啊、牲畜瘟疫啊什麼的。然而儘管如此,還是有那麼多的人願意在這裡繼續生活,並且也不認為受點天災有什麼太委屈、太想不通的。
蝗蟲也願意在這裡生活呢,草地一片一片地給它們咬得枯黃,於是羊就不夠吃了。蝗蟲真可恨,但也可憐。因為它們的初衷跟羊一樣,只是找口吃的而已。
比起蝗蟲,羊群的規模更為龐大,並且發展態勢更是不可阻擋。我們所有的行為都向羊的利益傾斜,其實是向自己的利益傾斜──我們要通過羊獲得更寬裕的生活,什麼也不能阻止我們向著無憂無慮的浪費一步步靠近。我們真強大,連命運都能控制住了。
蝗蟲來一撥,就消滅一撥。我們真強大,一點兒不怕它了。
可是,這是不祥的……因為蝗蟲仍在一撥一撥地繼續前來,並且越來越難以對付(名字也越來越神氣,什麼「亞洲飛蝗」啊,「義大利蝗」啊……)。自然界的宏大程式繼續有條不紊地一步步推進,無可抗拒。儘管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感覺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體驗些什麼。
*作者生於新疆,童年與少女時期不停輾轉於四川、新疆兩地,高中輟學後,曾隨家人於阿勒泰哈薩克村落生活;善於寫作,多年來已獲茅盾文學獎新人獎、人民文學獎、上海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天山文藝獎等多項殊榮,2018更以《遙遠的向日葵地》獲頒中國最高文學榮譽的魯迅文學獎